大学同学齐之谖给我发消息,问我周六晚上去不去杜的 party,说杜下学期可能就不在了。我回复他:一定来。 我刚在荷兰念完硕士回来,正在 VICE 实习。
我非常期待能见到杜。他是人,在师大做客座哲学老师,我们叫他杜或者大。我在大学最后一学期零零散散地旁听了几节他的法国哲学课。虽然是旁听,但杜要求我们做到和选课的学生一样,准时来,不缺课,按时交论文,否则就把我们踢出教室去。我们大半个学期都在读法国哲学家易·阿尔都塞。几次课听下来,我感觉自己只能吸收到之前已经懂的部分,几乎没有新的收获,于是畏难情绪就像清明节的黄酒一般上了头。我开始旷课,逃避杜。有一天好朋友 Leach 发短信来:你被杜点名了。
期中论文也是关于阿尔都塞的,英文写,只需要写1000字。我一晚上反复读了几遍《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找到了里面看起来很矛盾的一处,作为我的研究问题。因为字数很少,我那会又刚刚完成托福、GRE 考试,状态良好(就和刚高考完那会处在知识水平的顶峰一回事),我一小时草草写完,和室友去北门喝瓦罐汤去了。
一周后我收到杜的邮件,说要和我聊聊。我浑身冷汗,心想肯定完蛋了。两天后,我们在隔壁学校的咖啡店约见,他点了两杯意式浓缩(很欧洲人的习惯),我要了一大杯奶茶(很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坐在露天的椅子上聊论文和将来的打算。其实他觉得我的论文写得很不错,不过有一处论证存在问题,他让我好好想想,下次课问我。
事实上,杜成了我一整个美好夏天的起点。每次周三课结束后,他都会叫我们去东门外的破烂酒吧喝上一杯,因为周三在国际学生看来是小周六。那时候我不太愿意和一大群人聚在一起,觉得顺畅的对话只可能在两人之间进行。我婉拒了杜四五次,终于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就硬着头皮去喝酒,还跑去买了一杯番石榴奶茶,被杜笑话死。
那晚的体验非常奇妙。师兄给我们讲了几个经典的苏联笑话还有金手指的故事。杜给我简单地分析了我风湿的原因,有没有你不愿想起的事发生在雨天?疼痛有时候比你意识到下雨了更早地到来,而女性对此通常会更加。天空低垂,气压变低,呼吸也变得更加困难。 而那天我们读的材料恰好和雨有关(这是我自己的翻译):下雨了。那么就让这本书在谈论其他一切前,首先成为一本关于普通的雨的书。马纳勃郎西曾经发出疑问,为什么雨落向沙,落向,落向海。既然这雨从空中,可以润泽庄稼,实现其价值,为何它要作践自己,要到海中去,浪费在上和沙里。我们的关注不在于那样的雨,无论它顺和天意与否。
那个夏天最后一堂课后,杜要赶飞机回,我也要毕业了。我对和他相处的时光如此不舍,哭哭啼啼了很久。我们又去了那间破烂小酒吧 庆祝。大师兄试图转移我的注意力,让他来自马耳的同学跟我聊诗歌。气氛缓和后,他告诉我们,杜刚刚来的时候,就像士一般。每次来听课的人都不一样,他就每堂课都从头讲起。杜就这样了那么多年。
那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恐惧。如果要说实话,我出国留学的首要原因不是学知识,也不是旅游,而是逃离我的大学校园。大学的最后两年对于我来说常恐怖的,我至少有整整三个月时间情绪失控。每天出门都想把被子罩在头上,害怕做任何一个微小的决定,在食堂排队快到窗口了恐惧得立马逃跑。我和班主任打了几小时电话,去看了学校里据说很专业但我却感觉很的心理医生,始终困在这个中。
杜对我说:你到欧洲去,要去佛罗伦萨,去巴黎,去伦敦。去剧院、博物馆、。你得去体验人生,才能写出一篇漂亮的 proposal。 因为他的话,我在很的人生阶段看到了未来的一点可能性。原来我还可以做那么多事,我的人生还有一些可能。回宿舍后,我开始期待欧洲的生活,每周日去上一整天法语课,在笔记本上写下被种草的燕麦片品牌。
欧洲的生活和过去非常不同。我们没有校园,朋友们住在荷兰小农村的各个角落。冬天昼长最短时,白天出门还没有天亮,午后回家天就已经黑了。我一周只有三次课,其他时间自己一个人啃书。有时候非常孤独,一天内唯一说过话的人就是超市收银员,上也只能看到一两个人。我开始和邻居们一块儿聊天,做饭。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比较的性格在这个群体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常常暗示自己要乐观一些,不要想那么多,就像他们对我说的那样。
几个月的 乐观实验 之后我崩溃了,我在2017年的第一周里连续哭了七天。二月时我又经历了一次情绪失控,这一次我觉得我要辍学了。后来我被爸妈的安抚奇迹般地。再后来的几个月,我被导师批到觉得自己是智障,对轻飘飘的、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忧虑,我觉得我不太想活下去了。杜曾让我给他写信,我无数次想动笔,但我对自己始终不满意,想等自己过得好一些时再跟他 update。
六月份的时候,距离回国只剩下三个月,我的留学生活开始有好转的倾向。我把只写了一章的毕业论文抛在脑后,订机票去巴黎。我和好朋友去了新桥,在拉丁区的电影院看了《2001太空漫游》,喜欢上了这个午夜时分街上到处都是神游者的城市。没那么游客嘛,比荷兰城市有趣多了。
八月底,我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被导师夸是一篇非常哲学的论文,选题相当勇敢,而我是一位很有活力的学生。带着这个小成绩回国的时候,我的内心也开始好转,我开始承认自己的优点,不再无止尽地自己。又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 VICE,跟 Alex 实习 -- 她是性与性别内容的编辑。发表文章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读我写的故事,在评论区里看到很多理解我的人。作为一个作者,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但现在这个心理还算健全的我已经不太在意了。我过去经历过的那些,只被少数人知道的挣扎这一次成为了我的 优势。没有它们,我想我可能就没有资格来到这里。
他果真把我忘了,很尴尬啊!为了证明 我们的过去,我在全场目光的聚焦下把他说 你要去巴黎、伦敦、佛罗伦萨 的那段话大声地复述了一遍。紧接着是大家的哄堂大笑,然后陌生的朋友们开始打趣:杜好像也跟我说过这些啊。
那个晚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室友一块儿,试图和来 party 的朋友们都认识了一遍,尽管我一个名字都没记住。惊艳到我的有一个英国女孩。她因为偶然的机会喜欢上了中国哲学,跑到中国来学庄子。她不断地赞叹我把罐装啤酒瓶口的形状联想成自行车座,她觉得这种形象之间的联系就是庄子哲学的妙处。还有一位是 VICE 曾经写过 的 Hugh,那位在《猜火车》里跑过龙套的苏格兰大哥。他给我律的室友讲了讲苏格兰法律的神奇之处。
我听着他的反馈,又想到和杜的这些事,发觉抒情的人生就是一个笑话。嘿,你可能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最后还是没有给他写过信,现在觉得也不用说出这句话了。让木讷钝感的大智慧帮我笑对人生吧。到达这一天,和过去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有关,就像《罗拉快跑》那样不能修改任何一个细节。
d5gt.cn 指纹膜 共享纸巾机 赛车群 欢威 www.k6c8j.cn www.81pdp8.cn 特价团 德国塔诺五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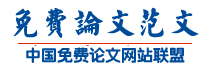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