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鸡的今年多大1964年8月所作《关于哲学问题讲话》是其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篇章,影响甚广。特别是《讲话》中关于只有搞才能搞哲学的观点,以及要用分析方法才能读懂《红楼梦》的论述,可谓独辟蹊径,别树一帜。《讲话》先在哲学界透风流传,初期出版的《思想胜利》全文披露。由于《讲话》内容及毛氏语言与当时气氛吻合, 因而迅速风靡全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初通文墨的人几乎人人皆知,奉为圭臬。
原标题:《关于哲学问题讲线月所作《关于哲学问题讲话》是其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篇章,影响甚广。特别是《讲话》中关于只有搞才能搞哲学的观点,以及要用分析方法才能读懂《红楼梦》的论述,可谓独辟蹊径,别树一帜。《讲话》先在哲学界透风流传,初期出版的《思想胜利》全文披露。由于《讲话》内容及毛氏语言与当时气氛吻合, 因而迅速风靡全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初通文墨的人几乎人人皆知,奉为圭臬。
吴江先生是此篇《讲话》的四个者和直接聆听者之一。2008年10月的一个周末,吴老在家中,向我敞开,娓娓讲述那些并非如烟的往事。
大凡人物提出治党纲领,必须要有理论作支撑。也一样,他的“为纲”学说的理论根据,是“一分为二”的哲学观。
杨献珍是一位老资格的家和著名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深谙思想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约在1964年初提出“合二为一”的哲学观。这一命题来源于明代哲学家方以智《东西均》这本著作,杨再用现代哲学思维加以发挥。显然,这样不由自主地使人联想到“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嗅觉敏锐的康生,立即将杨献珍在课堂上讲述“合二为一”的情况向汇报。毛其时已十分,马上:他这是反对我的。此话一出,杨献珍命运可想而知: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调出党校,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合二为一”论。
决定亲自介入此事,命陈伯达组织人马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他:要广泛收集,马列主义与资产阶级学者的哲学资料,看他们对对立与统一、分析与综合、矛盾等问题持如何看法。还说,所写的文章必须这些问题,从哲学理论上彻底驳倒“合二为一”。陈伯达领命后,指定吴江、关锋、龚育之三人完成这一任务。吴江,再增加《红旗》哲学组的邵铁真,陈伯达亦同意了。
我问吴老:“是不是因为您曾任过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陈伯达让您来领衔完成这篇哲学文章,这在当时是第一选择吗?”
吴沉吟片刻后说:“大概也可这么说,但也不完全是。陈伯达是《红旗》总编辑,但他不主持日常工作,日常工作由胡绳、两位副总编和几位编委轮流主持,我是管学术业务的编委之一,编委会还有王力、关锋等。”
吴江老继续告诉我:“在前几年写国际反修文章时,我与陈伯达接触日渐增多,也可说是频繁。他对我的思考能力是认同的,知道我不会去人家观点。所以陈伯达起草的文章,我可以尽情挑刺,不必;范若愚对马列主义著作熟悉,负责核对原文;记忆力超强,熟悉政策,但谋篇为文不是所长,他主要是参与文章讨论,在会上滔滔不绝,往往是的主角。隐隐约约,在当时《红旗》有‘四驾马车’之说。”
我大感兴趣。吴老说:“大概在1965年底,陈伯达通过上意,将一位副总编辑调配到广西任桂林地委副之职。过了些时日,陈伯达突然宣布《红旗》要成立‘学术领导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这个名单上没有任副总编的胡绳,也没有作为编委的我。没有胡绳可以理解,因为胡绳已是‘文化小组’之一,而没有我则引起不少议论,因为陈伯达平常写东西经常拉我参加,还是倚重我的。”
吴老继续说:“其实陈伯达为什么没有将我列入‘学术领导小组’名单,也算事出有因吧。陈这个人在生活上不大检点,不知不觉与一位女校对有染,且打得火热,并把她调入勤务组,大得很呐。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大概也给一个学生辈的人讲起过。结果那个人贴出了,说我吴某人上级领导。”
吴老承认,陈伯达还是很想让他加入“学术领导小组”的。为此,陈伯达专门找他谈话,告诉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我把你打入冷宫的原因。这样吧,你写点东西交给我,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小组了。”
陈伯达的做法使吴江十分反感,他对此根本不予置理。“小组”名单里自然没有“吴江”之名。开始后,《红旗》“学术领导小组”上述,均进入“中央小组”之中。
吴老诙谐地说:“这既是陈伯达帮助了我,也是我祖上,之中了我。看起来,诸暨人刚直的性格,有时还有好处。如果我稍稍服软,给陈写下片言只字,则立马进入这个小组。如此,我的后半生不堪设想,结果是他人之祸化作我人之福。我对陈伯达应额手。”
我们的话题重又回到陈伯达布置的文章写作上来。吴老说,完成这一任务,关键难处是不知从何着手。陈伯达语焉不详,没有交代清楚。他们四个人讨论了几次,商定还是围绕“一分为二”展开,在认识论上多做文章,为毛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提供理论依据。约在七月份,我们在完成了基础资料的搜集。其时在,我们就赶到去。大概在8月10日左右,我们将基础资料和文章撰写提纲,交陈伯达转呈送审。往后的几天是难得的放松,但也惴惴不安,因为我们要等待的,如何有针对性地亮明观点,写好这篇重要文章。果然,陈通知8月18日下午,毛要召四人谈话,陪同谈话的还有陈伯达和康生。
吴江老告诉我,“关锋是山东人,我是浙江人,邵铁真是哪里人,我记不起来了。龚育之是湖南人,能够听懂毛的湖南话,我请龚作记录。其他人准备专注倾听毛对文章的布置,因而龚是唯一的会议记录人。”说到这里,吴江老站了起来,从书柜中拿出龚育之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和《关于哲学问题讲话》的复印件。由此可见,为这次,吴老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吴老说:“我们按照通知时间到达的住处。兴致很高,笑容满面,挨个和我们握了手。我们也不拘束。然而坐下以后,他的开场白使我们意想不到。”
他介绍,毛一上来就说:“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我们满心期待毛对文章如何写作作,想不到一上来他就要我们立即下乡去参加。而突然的一句‘身体不好也去’,我们的思一下子跟不上。听到下面才明白,原来王光美此时已下乡搞‘四清’去了,与一个大队的人同吃同住,因为没有暖气,犯了两次重感冒。春节返京,王与碰了面。毛问她:犯病了还去不去啊?王果断地说:我还是要下去的,无非是发几天烧而已。真是女中豪杰。”
吴江先生明白无误地说,毛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不搞,搞什么哲学。”并且讲,现在的大学文科教学没有什么作用,所有文科的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都统统要下乡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去搞,那个是大学,什么北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毛还结合自身的经历说,“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在这次讲话中,还说:中国“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
谈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这个估计出于最高之口,使我们在座者很是吃惊。
四对我们上呈的材料和提纲如此评价:“关于哲学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提纲看了一遍(指“合二为一”论的文章提纲),其他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下。”
紧接着毛表扬了我们:“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当毛转入哲学话题时,我们兴致更高了,因为这是我们要写这篇文章的议题。但失望的是,刚刚切入不久,毛的思又跳跃式转到去了。最后天马行空,谈到如何读《红楼梦》上来。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只有用阶级分析,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四大家族史,才能读懂《红楼梦》,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
吴江先生钦佩地告诉我:的知识确实精深,他可以一字不漏地将“好了歌”背下来,可以把的经典理论、成语出处信手拈来,可以从别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的角度讲出新意来!《红楼梦》在全国一时如此普及,研究人员如此众多,与毛的这一讲话推动也不无关系。
谈话的结语,表面上是针对我们四个人说的:“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搞,才搞哲学。”可想而知,这一观点此后就不仅仅是在哲学界宣传贯彻了。
我们终于明白,毛此时对写哲学文章已不感兴趣,他要更直接的、面对面地搞;而且这一面对面的“斗争对象”,数量庞大,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或同情者。
“这两份资料都交给你,你回去可以对照一下,记录稿与发表稿还是有不少改动的。如陈伯达有好几处插话,但发表时陈的插话只出现一处。毛的有些话头,是康生在导引,发表稿有反映,但不多。我还注意到,这次谈话可能有秘密录音。”并把他在两份资料上勾划对照之处指给我看。
我突然冒昧地问吴老:“您这次没有写成哲学文章,但花了很大精力搜集材料和拟出了提纲,这是不是与十多年后您与杨献珍那场学术纠葛有关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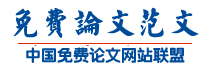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