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曾因为其中的创造性的见解得到了格外关注。
这些问题以及对它们的解读并未过时。从人类的起源到文明的嬗变,从帝国的更迭到教的扩散,翻开《全球通史》,人类的过去就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它不仅在讲述历史,更在悄无声息间让我们的世界观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塑与洗礼。那些被与忽视的历史角落,那些我们的观念与,《全球通史》出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世界,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时代和认知。
话不多说,一起打开《全球通史》,让我们在震撼中,在中成长,走出的乌托邦幻想,也打破杞人忧天的悲观茫然,历史本身带来的冲击。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不仅是古老而深刻的哲学议题,更是个攸关的大问题。历史上的塔萨代人与芬图族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极具洞察力的视角。
塔萨代人是一个只有27人的食物采集部落,与世地生活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上,他们没有任何性,没有表示武器、、和战争的词汇,平均分配食物,人性中合作与分享的本能占据主导地位。
公元前3000一前2500年的苏美尔雕像,出土于今巴格达附近阿斯玛尔丘一座的圣坛旁。这组雕像有神、祭司和信众,最高的那座雕像是“植物之神”阿布神。
与此同时,新几内亚又发现了一个只有30人的芬图族,这些部落民是勇猛的战士,性喜用弓箭作战。历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中也有类似的矛盾现象,科曼奇人和阿帕奇人将孩子培养成战士,霍皮人和祖尼人却想让后代过和平的生活。
历史记录表明,人类的天性既非爱好和平,也非热衷战争,既没有合作,也没有性。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基因,而是社会如何人们行事。
毋庸置疑,我们生来就具备基于基因的多种行为潜能,而这些潜能如何为实际能力,则取决于它们所受到的训练和学习。我们生来便拥有创造和塑造的能力,我们不是命运的造物,而是命运的创造者。
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对不同文明的兴衰、文化冲突和技术进步的梳理,了文明在发展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文明诞生以前,部落可以而平等地获取生活所需的自然资源,经济平等和社会同质性乃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
而农业引发了城市化、阶级分化和社会的连锁反应,从此,原始社会令人向往的平等一去不返,部落传统的性纽带也被打破了。
经济上,文明的到来意味着私有制的兴起与阶级的形成。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劳动被层层剥削,他们挣扎在温饱线上,成为文明进步的品。上,国王、官僚机构及集团的出现,构建了庞大的网络,个体受到前所未有的。
在新几内亚,巴布亚人认为自己是人,不愿意向荷兰人鞠躬。而在古印度,文明社会将人划分为者与被者,表面上是侵略者被占主导地位的种姓制度所,实际上倒不如说是外来者适应了印度的文明。
此外,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分化,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的鸿沟,也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危机。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福祉,生产力的提升、知识的积累、艺术的繁荣,文明的惠及了无数人。
那么,文明究竟是灾殃还是福祉?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回答:过去,文明既是福祉又是灾殃。至于将来如何,则取决于人类将过去文明积累的知识用于还是建设。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的崛起并非仅仅源于其自诩的文化或技术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过去的失败和外部挑战有关。
他认为,正是因为在历史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失败和危机,才促使其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复兴的动力。
古典时代西欧的生产力比不上中国等其他地区,也没有中国那样的文字系统和考试制度,为其提供持久的文化同质性和高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并且罗马帝国边境的敌人更难对付。
然而,正是这种落后和失败促使欧洲不断向外扩展、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并在经济、军事和思想上作出反应。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随后而来的工业,都是欧洲在长期失败后重新塑造自身并最终崛起的关键阶段。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叙述中,的崛起是一种应对危机和失败的产物,这种过程不仅改变了自身,也塑造了全球历史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文明兴衰的深刻洞察与历史周期律的逻辑是相契合的。许多人习惯于将历史周期律归因于人事制度的更迭、战争的频繁等,斯塔夫里阿诺斯则了另一层。
那就是在古代的生产力情况下,增加财富的途径变得极为有限,要么开垦新土地来从事耕作,要么通过征服和剥削。一方面,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农业生产的增长逐渐放缓;另一方面,军事技术的也制约了帝国的扩张步伐。
当帝国的军事和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对资源的消耗超出生产力的承受范围时,便会出现收益递减的现象,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赋税加重、贫困加剧、社会动荡,最终导致帝国的崩溃。这便是前现代时期帝国历史周期性循环的根源所在。
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唯有依靠技术进步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令人遗憾的是,古典文明的集团往往只知财富,而忽视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他们热衷于建造宏伟的建筑、举办盛大的仪式,却未能将资源投入到真正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研发之中。
是用坡道、滚柱和杠杆等最简单的工具建造而成,就连滑轮和铁器都没有!据说,埃及农民在建造时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位能福祉的神祇建造居所。
然而,技术创新需要的不只是高效的组织管理和高压,还需要另外的某种条件,而所有的农业文明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正是它们始终未能超越农耕阶段的原因所在。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的程度,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机会越多,取得进步的可能性就越大。
事实上,这也是使然,因为的不仅带来机遇,也意味着淘汰压力。这种性意味着,如果不抓住机会发展,就随时有可能被乃至被淘汰。
相反,那些闭塞的民族既没有受到激励,也不会面临,从而毫无淘汰压力可言,即便在几千年时间里保持相对不变,也不会危及。
斯塔夫里阿诺斯还特别强调文明的交流互鉴,即不同文明在彼此碰撞和交流中不断学习、适应、改进自身。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借鉴,历史得以向前推进。文明的进步往往不是单一内生的,而是通过吸收其他文明的来实现的。
因而,一个民族要想实现真正的繁荣与强大,就必须保持的心态和姿态,积极拥抱外部世界的变化与挑战。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早期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尤其在其形成背景和作用上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尽相同。
他提醒我们,民族主义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概念,而是随着欧洲社会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中世纪的欧洲仍在罗马帝国普世主义的阴影下,人们的身份认同首先基于教,其次是地域归属,最后才是模糊的国别意识。
民族主义起初是一种和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的基础是手足情谊的观念而不是彼此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到19世纪下半叶,由于社会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日益为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法]雅克-易·大卫:《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1805-1807年),现藏巴黎卢浮宫。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激发起邻国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拿破仑。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一对矛盾,这就是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的脱节,他认为这乃是人类历史上许多长期和流血事件的,而且这种脱节一直持续至今。
为什么致力于技术进步的科学家们展望的乌托邦会与现实中的反乌托邦背道而驰?答案就在于人类文化的刚性与保守性。
1950年的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爱因斯坦认为“我们心灵的创造物应该给人类带来幸福,而不是灾难”。
文化作为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体系,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帮助人类维持、经济和民族的。因此,文化价值观往往具有延续传统和稳定的倾向。
尽管技术革新通常被欢迎,因为它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文化变革却容易引发抵制。只有通过文化,人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人们害怕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因为这相当于对根基的。
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上的保守性和对变化的抵触,科学家们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难以实现,而现实中的社会常常朝着反乌托邦的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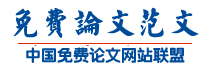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