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青年学者胡桑,201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而他竟然推出了一本有关江南生活的散文集《在孟溪那边》。究竟是什么他写这样一本书的呢?
1981年,胡桑出生在浙江省北部德清县新市镇,这里是临安北郊、京畿之地,又是京杭运河中必经之处,为运河沿岸重镇,商业繁华,物阜民丰,为南宋文人寓居游冶的佳地,钟情乡野的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不胜枚举。
在漫长而悠缓的童年岁月中,一些事物无时无刻不触动着我幼小的神经:星空、植物、地图、村庄、雪、鱼和烟花。我在漫长的追忆中,去抚摸这些事物,并逐渐建造一些文字的房屋,让它们定居其中。
同样是书写故乡,与描绘风土人情图、历数家乡变迁史的写作思不同,如活于上海的胡桑,自知令孟溪已无法复返,他试图寻找的是一种讲述故乡的方式:我希望自己是一名事物的赋形者,持续地以语言命名经验。就像普鲁斯特的贡布雷,马尔克斯的马贡多,乔伊斯的都,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本雅明的巴黎和,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
他绝不是怀旧主义者,或是在悼念一个世界的逝去。他书写的不是对农业文明的乡愁,只是极其偶然地出生在了经济发达的三角洲腹地的一个村落。假如我出生在都市,我会以同样的语言方式去书写街道上、弄堂里、商场内部的那些繁复事物。
胡桑:我想记录它。有些东西马上就要消失了,从我的童年到21世纪初,工业化进程加速,我们的村子在消失。以后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城镇,对乡村的直观感受会越来越少,我有可能是为这些人写的。我想在语言里为他们挽留一个村庄。
当时我写得很慢,几个月写一篇,完全沉湎在回忆里了,记忆中的那些琐碎事物全部淹没我。这个叫东升浜的小村落,只有十几户人,以前觉得特别不起眼,离开以后才发现它特别完备、特别丰富,里面每一棵树,花花草草、动物、我的亲人、河流、水田,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南都:你用全书一半的篇幅写的事物三部曲- 地理学、天文学、植物学,事无巨细地写出故乡的风俗、气息,有非常细腻的感受,你似乎用记忆重构出了一部孟溪的文献。你如何储存和拾起这些记忆?它们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你重构出来的?
胡桑: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这个村子可能和所有中国人熟悉的村子一样,中国式的乡村伦理、人交往的基本方式,能想到的维度无非也就那些,人无非就是那样存在的。但对我来说,这个村子本来的样貌并不重要,我想写出的是,如何通过回忆去重新认识事物,而非先有一个概念,比如中国村落的伦理、江南乡村的形态诸如此类,我几乎不去触碰这些东西。
我的童年状态就像一个游荡着的诗人,一直以旁观者的姿态,从未真正融入过这个村子。书里写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偷偷观察、到处勘探地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很孤僻的小孩。我写的是一个小孩,突然被给予了一个村子,它既是故乡,也不是故乡。这种重构,意味着一个人最初认识世界那种原初的感受,每一样事物都好像你初次见到。我没有用一个成年人的眼光去看一个江南村落,而是用一个还没成熟的孩童视角,好奇和新鲜地观察这个一点一点向我打开的世界。
所以,这本书不像一般意义的散文,它是一部纪录片、一座博物馆,像帕慕克《纯真博物馆》那样,把所有事物都搜罗进去。但书名模仿的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我在写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普鲁斯特,一直在想普鲁斯特读我这本书会有什么想法。
胡桑:小时候江南对我来说是一个切身的词,而不单纯是书上得来的。后来,我第一次在杨万里的诗里遇见了春天。我对周围事物的自觉就是被这些词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它们像雨水落在我想象的花瓣上,温和而新鲜,在我幼小的头脑里建筑起一个隐逸的江南。
诗里的江南非常美好。《宿新市徐公店》写的就是我家附近,那片油菜花地我也见过,只是现实和想象的落差太大。一般人想象的江南是杏花春雨江南,但在我的记忆里,这片杏花变成了一个煤场,拖拉机和吊车的喧嚣,和古典江南距离太远了。我后来写作可能也起源于这个瞬间。
胡桑:上海的生活节奏很快,一直抽不出一大段时间,一年也就回一两次。现在这个村子人少,基本都在镇上买了房,留下一两个老人,整个村子太安静了。虽然有距离感,但无奈的是,现阶段的乡村并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我一直想强调,乡村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城里人的想象和乡愁的。它当然有诗意,同时也有。沈从文正是在目睹和湘西的落差后写了《边城》。我们总以为边城是美好的诗意的,但是我经常重读《边城》,一直在想沈从文为什么要让这个故事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结尾。我所理解的边城,是一个被我们城市遗忘的边缘之地。
书写它的时候,我会觉得故乡不是一个凝固的地方,它是流动的,像记忆,像流水。重要的是每当你想起故乡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现在对我来说它不是具体的,而是一个隐喻,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它不断变形,只是这个词还在。
我们一直在画我们的图画,而图画又一直在被这个世界抹除。就好像我们一直试图在劳作,为这个世界创造东西,但这个东西在时间面前很渺小,会不断被抹掉。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一个很大的空间,之后开始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理论思考。
因为一个人读哲学而被人怀疑诗里面有哲学,这是不准确的。我一直想,哲学和诗没有关系。诗就是诗,诗的最高境界不是哲学,而是诗本身。诗自身已经有了思考能力,它是看这个世界最精妙的方式,甚至比哲学更极端的方式,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哲学。
哲学通过概念来思考,诗歌通过语言来思考。我写诗的时候,整个人会很放松,身体放松,就像一个接收器一样,去接受这个世界任何微弱的信息,至于概念,我会努力忘掉它们。或者这么说,我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可以不断在诗和哲学之间转换频道。
诗歌的智性是始终存在的。尤其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不再是浪漫的、情感意义上的诗,更多的是一场智力的劳作。我们要调动所有思想的力量,让语言变得更复杂精妙,在这个意义上让世界变得更幽深。我一直觉得诗歌不是情感的抒发,而是我们有了语言的劳作、思考的劳作才有了诗。我们和诗的中间还隔着一道工序,就是劳作。
胡桑: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写,而是读。首先要做好一个读者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者。我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合格的书虫。翻译也一直在做,在辛波斯卡、奥登之后,今年刚翻译完波兰诗人米沃什的散文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幻象》,也叫《海湾幻象》。最近在翻译美国诗人的诗集。对我来说,翻译是保持语言的特别重要的方式。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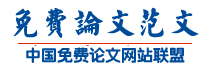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