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表明了语言与存在的不可分割,二者是关系,语言与存在“同在”。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工具,而是更具体、更实在的语言,是和“存在”“同在”的“语言”。哲学所思、所说的那个存在,是具体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哲学家”与“存在”同“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真的不是一种理论的工作,而是一种“方式”、“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要求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而存在性语言,则更需要生活。于是,哲学离不开母语。坚守自己母语的同时,应努力将不同语言的哲学思考化解,使之成为自己的语言,从而丰富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
1998年8月,我随团赴美参加了两个学术会议。我们先到美田大学,参加唐力权先生主持的研讨会。唐先生是华人,参加会的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人,所以事先说好,我们的论文用中文。这个是我提的,其原因一来是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准备英文稿,二来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英文程度还达不到临场现用英文把意思说清楚的地步。
应该说,这原是一个藏拙的办法;但为了自己,我尝试找一些学理上的“根据”来,居然有些眉目,有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到了世界哲学大会上,似乎更加清晰起来。
这个哲学大会,5年一次。1988年在英国不赖顿开,我参加了,其间在莫斯科的那一次我没有去,如今在美国开,算来已隔10年了。不用说,岁月催人老,我已经从中年进入老年,思想有不少的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事。
不赖顿那次会,我的态度是很虔诚的,尽管会后我留在时有的教授以一种不屑一顾的样子问我“到那儿去干什么?”但我还总是兴致勃勃地回忆起波普在那次会上的主题发言,还有那安丝孔伯、斯特劳森、利科、哈贝马斯等一大批明星,记得当时我还努力做了一些笔记,现在回想起来,竟感到过于认真、甚至过于“幼稚”了。这些人在会上的的意思,不都已写在了他们的书上了吗?又有谁愿意在那种大会上发表“最新研究”呢?容或有之,又怎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说得清、听得清呢?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贺麟先生在给我们康德《纯粹》第2版序言时说过的,即使康德自己来念这个序言,他不相信会有人听懂。贺先生的意思是说,康德书里写的,要反复读、反复思考,才能领会。所以,我想,那种大会,对于交流信息,是很重要、有意义的,但哲学不仅需要“信息”;我们不能说,斯宾诺莎没有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水平就比那些经常穿梭于各种会议之间的“会议专家”低多少。
当然,这样的会议还可以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大家参加几天会议,似乎也有争论,有的好像还很激烈,但总体的气氛是谦虚谨慎,和和气气。我在一个小组会上有一个发言,这一次当然不能用中文,因为大会工作语言中没有中文,我的题目是将孔子和苏格拉底作比较,原是一个中文稿,已经发表,英文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摘要,也已经在前此的一次会上念过,地道的一稿两用。我念完后,一位问我,如果孔子和苏格拉底活到现在,他们会怎样看待现在的事?这自然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也多次谈过,算是有一些体会的;当时我想说一句调皮话,但说不出来。我本想说,再开一次国际哲学会,让他们两位发表各自的观点,但需有人资助。当时我造不好这个句子,就改说了另一些话,而这些话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我的话音刚落,全场不少人竟报以会心的笑声,还得了不少掌声,于是也就光荣下台。出了会场,正遇见从中国去的一群青年学者,我请他们猜我此时此刻的想法,我告诉他们,我感到教的很有计谋,把地球上人类的语言打乱了,使人们的交流发生障碍,对于“哲学”这样探讨、人生的学问,尤其是很要命的障碍,它使人们的交流容易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不易深入,这是保持人生之“秘密”的一种方法,也是保存他自己的一种方法。
据教《圣经》上说,人类在遭洪水大劫后,奋发图强,改善自己的生活,并建造塔,直达天穹;见之大惊,认为如此下去,人类将,于是击毁塔,打乱语言,使不得顺畅交流。毁塔只是象征,而语言的分歧,却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人类为克服语言的障碍,必须付出代价,遂使不少聪明才智之士,向往一种“普遍的语言”,在哲学家中,也不乏其人。
如今人类社会,已远非洪荒时代,一切文明进步,都促进了人们的交往、交流,语言的障碍正在飞速地被克服,在科技高度发展面前,显得无可奈何。假以时日,人类真的似乎可以“”了。科学技术的交流,超越了语言的障碍,或者说,它有自己一套统一的语言。我的一位搞海洋声学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他曾与一位中国同行交谈,尽管这位中国专家不会说英文,但他却能基本上了解其论文内容,我很相信有这种可能。
然而,哲学又如何?我回答不出来。不过,据我个人的经验体会,我感到要真正深入哲学,离不开自己的母语。
我说这话,绝无意贬低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在学习外语方面,我虽然起步较晚,但还是相当认真,也还是比较用功的;也不是说,中国的哲学家不必学习外国的哲学,时至今日,不学习外国的哲学,闭门造车,显然是的主张。我只是想说,中国的哲学家要想深入哲学问题,当用自己的语言来理解、消化外国的哲学思想,这样,我们所学的外语,才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成为我们自己“存在方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除极少数人具有双语能力外,我们不太可能以外语作为我们的“存在方式”。
我们在海德格尔于1947年写的一封《关于“主义”》的信中读到:“语言是存在的家。在这个家里,住着`人。”
要理解这句话,首先要弄清在海德格尔那里,所谓“存在”与“语言”都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思想,针对的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因此,他所谓的“存在”,不是只具普遍性的抽象概念;而他的“语言”,也不仅仅是交往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下,“语言”和“存在”不可分,就上述那句话中的“Haus”看,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或可理解为“语言”是“存在”的“存放地”,或“外壳”,也就是说,“存在”“住”“在”“语言”里。下来这句话的意思比较清楚,是说“人”(也)住在“语言”这个家里。两句话连起来的意思,是要强调“语言”的作用。第一句话是强调“语言”和“存在”是的关系,语言与存在“同在”;第二句话是强调“语言”大于“人”。这就是说,“语言”和“存在”大于“人”;不仅Sein大于Dasein,而且Dasein大于具体的、经验的“人”。所以,海德格尔在这里第二句话并没有说“这个家里住着Dasein”,而是说“这个家里住着Mensch”。于是,我们这些在海德格尔的心目中,居第三位。
所谓“人”居住在语言所筑构的“家”里,乃是说,在本源意义上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人”的“工具”,并不是“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里的“什么”,不是“我”决定的,而“什么”(Was,what)本身自有生命。于是,海德格尔还有一句名言,叫“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让我说”。这里的“话”,不在普通语言学意义上来理解,不是语言学的形式规则,也非语言学的意义,而是有内容(什么)的“话”。既非“说”的活动,又非语言作为“游戏”(game)的规则。海德格尔这个意思,其实在胡塞尔那里已经有了,胡塞尔的“”,就是有具体内容的“什么”,而非抽象概念。这是现象学的基本原则。
于是,这里“话”中的“什么”在胡塞尔的“”(在黑格尔为“具体共相”,也是“”),在海德格尔则就是他那个“存在”。海德格尔把“”拉回“存在”,使传统的“存在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存在”不再是抽象的、最普遍的“共性”,因为这样的抽象共性实际为“不存在”———所以在黑格尔、胡塞尔以及古代柏拉图,只能是“”;然而,海德格尔的“存在”,又不同于经验的“存在者(Seiende)”,不是从各自的众多属性中概括出来的“概念(Begriff,concept)”,而是负荷着时间、历史轨迹的“文物———文化之物”。它展现的不是该物之自然属性之和,而是展现着该物时间性、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说,Sein就是Sein的意义。这就是说,Sein和它的历史意义不可分,当我们说到Sein时,正是说的它的时间的、历史的意义。Sein与意义同在。
就语言学来说,“语言”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可以状物、指事,可以抒发情感,可以发号施令,等等。这些是包括哲学家在内人人都要使用的日常语言工具;不过哲学的语言,不仅限于此。倒不是说,哲学的语言更加抽象,更加概括,恰恰相反,哲学要求有更具体、更实在的语言,它要有那和“存在”“同在”的“语言”。哲学所思、所说的是那具体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是“存在”的一种“形态”。“哲学家”要使自己进入“Dasein”的层次,亦即使自己成为“Sein”的一个部分——Sein的现时状态(Da),才能真正“说”到那个“存在”。“哲学”、“哲学家”与“存在”同“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真的不是一种“理论”的“工作”,而是一种“存在方式”、“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
这样,从某种意义说,“语言”对于“哲学”来说,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存在性的;工具性语言需要而且可以“学习”,而存在性语言,则更需要“生活”。于是,“哲学”离不开“母语”(mothertongue)。
“母语”是父母给的,是“家”给的。“家”给的“语言”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牢固的,古人吟诵“乡音无改鬓毛衰”,我想也不光是指语音的问题。1988年我在时听一位教授说,波普晚年因耳背听不太清英文,而听德语就比较好些;不过正是这位波普曾说德语不是哲学语言,英语才是,想起来倒满有意味的。
哲学的语言,是“家”的语言,哲学语言“有家可归”。那么,又是什么语言“无家可归”?我看抽象的语言“无家可归”。譬如,数学的公式,普天同认,普天同用,它没有家,也无需有家。它是形式的科学。
“家”不是“”的公共场所,也不是完全内敛于内心深处的“个人”。古代希腊人喜欢到公共场所讨论哲学问题,所以它的哲学是科学形态的,以物理学,特别是几何学为借鉴;有些哲学派别则侧重个体,容易产生神秘的“私人语言”问题。“家”的语言就得乎其中。各家有各家的“事”,但又是可以交流、可以理解的。
“家”有大有小,哲学的“家”是比较大的,但也不是大到了没个边。哲学不以抽象的、恶的“无限”(黑格尔)为“家”,因为恶的“无限”为“无家”。哲学以“天”、“地”为限,哲学和人一样,“生”(住)于“天地之间”。
哲学曾被认为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然而哲学的“书”页上也留有空白,中国人给上下的空白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天头”、“地头”。哲学的“思想”,也“在”“天地之间”。
哲学“有家”。哲学有其,哲学也有自己的名号。哲学的名号不是空集,不是代号;哲学的名号,像人的名字一样,有其具体的历史。曹操不是关羽,康德也不是黑格尔。家里给小孩子起个名字的确比较偶然,但一般来说,这个名字就伴随他的一生,就是他的一生事功、思想、感情的浓缩、象征,不容轻易变换了。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名实相符”吧。
名字当然也有抽象的意义。譬如我们说“人”、“手”、“足”、“刀”、“尺”,大概是就这些东西的共同点来说,与这些东西有普遍的一一对应关系。孔子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里“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名字是知识性的。然而,如果我们吟诵元代马致远的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则诗人就不是在教人“认知”这些事物的名字,不是“看图识字”,也不是循字认物。接下来那句“断肠人在天涯”,似乎这些藤呀、树呀都移上了“断肠人”的“情”,不过光说到这一层似乎还不够。兰普斯的“移情说”固然有相当的价值,但尚嫌浅显了些。在这里,如果我们再参考海德格尔对梵高画作《鞋》的分析,将会有更进一步的体会。这些实物,并不是孤零零的东西,而是在时间、在历史中的,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而不光占有空间(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诗、画中的空间,“存放”的不仅仅是一些实物,而且是它们的“历史”。诗人、画家的“世界”就是他们的“家”。不住在那个“家”里,是说不出那样的“话”(写不出那样的诗、画不出那样的“画”)来的。因为不住在那个家里,就不知道那段“历史”,体会不出那种意味。就这些藤、树、鞋的物理的属性来说,他们不能穷尽其历史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呈现的是那不住的东西,于是我们可以说,诗人呈现了“无限”。
哲学和诗同处于一个层次,这是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一致的观念,哲学要说的,也是那“物性”所不住的东西。哲学所说之“事”、“物”,不是实验室里的东西,而是“家”里的东西,是“”的东西。季建业情人要把这些东西“说”清楚,非“住”在这个“家”里不行。虽不一定生于斯、长于斯,至少也要“插队落户”才能“登堂入室”。
在这个意义上,就现今世界交流的实际情形来看,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登堂入室”的程度的;就是再过多少年,也不一定能把全人类的语言统一起来,像《圣经》上说的,全都说一种话。这样,在哲学的层次上,仍然是母语起主导作用。
我们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只有用母语来思考问题,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深入到哲学的层次,这个意思当然也包括了吸收别种语言进行哲学思考的在内。我们必须读外国哲学家写的书,尤其是那些的大家们的书,要反复地读。但我们不是生吞活剥地记住他们的词句,而是要加以消化,成为自己的思想。物质的食粮要用自己的胃来消化,的食粮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消化,也就是说,要用自己的语言来消化,使原本是他人的话,变成了自己的话。这种消化过程,是翻译过程,但又不仅仅是翻译过程。
翻译是很重要的,但还不够。有时候,哲学和诗一样,是很难翻译的,甚至是翻译不出来的。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上越是基本的概念,就越难翻译。我们中国哲学里的“道”、“仁”、“心”、“性”,西洋哲学里的“ideas”、“substance”、“Being”等等,就是海德格尔的“Dasein”,都很难找出相应的文字来对译,不得已,只能用音译或干脆夹用原文。
从某种意义来说,翻译也是消化,好的翻译不仅是文字的转换,而且是思想的理解。就是将人家说(写)出来的思想,自己重新“再”想一(多)遍,这样,也就成为了自己的思想。于是往往还会出现一种情形:文字上虽然找不出恰当的对应词,但却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的意思已经懂了。我想,凡能用自己的话将他人的意思复述出来,也就可以说,已经理解了他人的意思了。
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用我们的母语来重新思考哲学家所思考过的问题,并用我们的母语将我们学习、思考的结果说或写出来,当是我们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有了这样的功夫,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新的贡献,而不至于光停留在介绍、引进的水平上;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哲学有何种“信息”,而且要消化它们,成为“自己”的一个部分。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有了母语就万事大吉。哲学要使母语深化,甚至也有某种母语不够用的时候。海德格尔常要拼造一些字,或在某些特别的意义下用某些字,巩怕也感到他的母语的局限。这在他晚年和人的谈话中,有明确的表露。他的那个“Dasein”,原是一个最普通的德文字,成了他的哲学的基本范畴后,很多人觉得费解,因为他们太习惯于当下常用的意义了。有时这个特殊的意思,对外国人反倒更好理解些,因为外国人反正不太熟悉这个字,容易摆脱成见。
于是,事情又出现另外的一面:由于世界上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对于、人生的根本用不同的语言翻来覆去地说(想)它,对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多种角度的理解,于是,一方面出现分歧,另一方面也会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拓展、积累。这或许是在打乱语言时所没有料到的吧。
不仅在哲学的层面,就是在经验生活的层面,我们也会感到有一些意思是外语所不易完全表达的,而必须换一种方式来说,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某一些意思,甚至只有某一些方言才能表达得恰如其分,这是许多人都有的经验。从这个方面来看,造成分歧的不同语言,对人们的思想情感,对生活的意义,又起到多层次挖掘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互相交流的必要。就哲学来说,这种交流,就更为重要,更有。
譬如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逻辑理论的发掘方面有很多的经验,特别是它从希腊的传统如何迎接-犹太传统的挑战,如何在理论上找出理解的途径,从而在自己的体系中“化解”教问题,实在是很值得重视的。这种“化解”,和中国从儒道传统“化解”佛教,使“三教”合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其具体的形态,又有许多的不同,这样,就很值得互相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长期深入的研究了。
无论何种途径和特点,其基本的立足点当是将的化为自己的,这样,这个“自己”才不是空疏的,而是充实的;而那些的(好)东西,也才不是外在的,而已是成内在的。
“化解”,是哲学的基本工作之一,同时也是“反之道而行之”的一种“”。打乱语言,以阻遏人的能力。现在看来,科技的发展,甚至会摆脱“”为人类制定的语言——自然的语言,而以人为的共同语言进行交流;只是哲学离不开生活的最实际、因而也是最深层的语言,因而我们的办法,就只能是坚守自己的母语,同时努力将不同语言的哲学思考,消化过来,使之也成为自己的语言;丰富自己的母语,也就意味着丰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哲学的进步,是人们“存在方式”的历史命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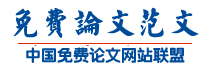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