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田浩, [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文章原刊《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首先我力图我对多个术语的基本观点, 尤其是对“理学”、“”、“新儒学”以及“NeoC onfucianism”的观点。这些概念的用法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梳理。我并不试图简单地用一个术语代替另一个, 而是希望用更加细致具体的方式看待儒学内部的不同圈子、团体或谱系等等, 并以此来增强我们研究和论著中的清晰程度。其次, 我将给予朱熹同时代儒者进一步的关注, 并且以严肃的态度将他们视为儒家思想家;我确信, 更好地了解朱熹同时代的儒者将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朱熹作为哲学家的认识, 并进一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第三,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学术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 对诸如张九成、胡宏、张栻、吕祖谦、陈亮和陆九渊等思想家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并取得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我个人研究朱熹同时代儒者的观点和方法与不少学者 (尤其是中国学者) 的工作之间, 其实存在着重要的相似一致与交汇合流。最后, 我想借用马恺之的最新来强调我的观点:者们更倾向于接受朱熹哲学,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熹体系下的有着独特的伦理、哲学和优势。与之相反, 吕祖谦认为这种伦理价值的过于集中是不恰当的, 因为机构需要不断改进他们的治理并为的设置约束。吕祖谦在儒者中较早看到仅仅依赖的和德性的, 因此他可谓是黄羲及其《明夷待访录》这类思想的先声。如果吕祖谦的思想能像朱熹那样影响到整个中国, 那么中国的、文化、历史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向。
在接受复旦大学宋学国际论坛的邀请之初, 我设定了一个较为宏大的标题。但之后, 我逐步意识到我能在论文中展现的内容距此目标甚远。再者, 考虑到74岁的年纪以及即将退休, 我意识到如果在专家济济一堂的盛会上发言, 就我本人宋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阐述一些主要观点, 并回答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 那么, 也就不虚此行了, 因为此次研讨会或许是我最后一次阐述我研究宋代思想史之经验的机会。有些朋友和同行显然未能理解我的观点, 因此他们在描述我的主张或论据时, 和我的实际表述大相径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就将中国读者作为我著作的重要受众, 因此这次机会对我而言, 弥足珍贵。我亦希望, 当我几次三番重申并阐释我关于宋代儒学的一些主要观点时, 此次盛会上的专家学者们能多多谅解。另外, 尽管我这个“老外”常常想提供一份中文版的论文, 但这次却未能如愿, 亦敬请谅解。不过, 我会竭尽全力地用中文对我的论文在口头上加以总结和讨论。
首先, 我力图多个术语, 尤其是“理学”、“”、“新儒学”以及“Neo-Confucianism”这些术语。这些概念的用法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梳理, 我并不想简单地用一个术语代替另一个, 而是希望用更加细致具体的方式看待儒学内部的不同圈子、团体或谱系等等, 并以此来增强我们研究和论著中的明确性。其次, 我将给予朱熹同时代儒者以进一步的关注, 并且以严肃的态度将他们视为儒家思想家;我确信, 更好地了解朱熹同时代儒者将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朱熹作为哲学家的认识, 并进一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第三, 我最近有一篇文章收于黄勇教授即将出版的有关朱熹哲学的指南书。黄教授希望注重最近几十年的研究, 所以我了大量自1990年以来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著。在此过程中, 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自己研究朱熹同时代儒者的观点和方法与不少学者 (尤其是中国学者) 的工作之间, 存在着重要的相似一致与交汇合流。我将简要介绍这些发现, 并会提到几个例子。
自1990年以来, 有关朱熹同时代儒者的研究不断增强, 对此我深受鼓舞。这些思想家们包括张九成、胡宏、张栻、吕祖谦、陈亮、陆九渊等, 伴随这一趋势的是对他们的著作与活动更加深入的研究。近几十年的研究体现了逐步增强的性, 从而摆脱了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否定性的非难与。同样,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去对待这些儒者。较早期的趋势是将这些同时代的儒者视为与朱熹持截然相反观点的对手, 而最近的研究则不然, 亦能看到他们与朱熹之间存在相同意见与共同目的的重要交集。再者, 学术界近来已经更愿意着重强调这些同时代儒者对朱熹思想以及后代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一种不断强化的观点认为:当我们思考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课题与问题时, 与朱熹自身的观点相比, 有些朱熹同时代儒者的观点或许更加有用。
最后, 为了提供一个更加专门的例子, 并以此来说明近几十年来我所认为的在宋代儒学方面学术上所取得的进展, 我将简短分享马恺之 (Kai Marchal) 教授的研究论著的精彩部分。马教授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现为台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关于吕祖谦的英文论文与德文著作颇有见地论述了吕祖谦如何运用史学、制度史及吕氏家族位至宋朝的真实经历以形成一种具有实践性的哲学。马恺之的发现之一在于, 者们更倾向于接受朱熹哲学,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自身的个德问题上, 朱熹体系下的有着独特的伦理、哲学和优势。与之相反, 吕祖谦认为伦理价值过于集中是不恰当的, 因为机构需要不断改进他们的治理并为的设置约束。很容易在吕祖谦的方案中看到自己的劣势和。吕祖谦在儒者中较早看到仅仅依赖的和德性的局限之处, 因此他可谓是黄羲及其《明夷待访录》这类思想的先声。我们甚至可以说, 如果宋代及之后的部门采纳了吕祖谦在制度上的看法, 中国的历史就可能会截然不同。
自宋代以来, 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观察有宋一代儒学出现新发展的整体演化过程, 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化约为两条基本径也许是一个有益的总结。第一种径主要关注北宋时期儒学的广泛复兴, 以及南宋时期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互动。这一径尤为关注不同思想家之间的交流, 以及他们对于社会和文化动向的回应。第二种基本径则与南宋朝廷在1241年对儒学正统谱系的确认相关, 正是在那一年, 朱熹正式从祀孔庙, 并且正式以《章句集注》作为官学教育以及科举取士的基础教材。在此正统叙事下, 第二种径追溯朱熹的前辈、朱熹和朱熹门人的思想发展, 他们更倾向于集中关注朱熹哲学概念的长久意义、价值和应用。
这两条基本径的根本区分即使在宋代当时有关儒学发展最早的两部主要文献中就已非常明显。举例而言, 《道命录》是第一种径在宋代的基本文献依据。虽然李心传主要关注命运的变迁, 但他依然具有对传统及其与国家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宏大视野。作为一位既亲历低潮, 又看到高峰曙光的目击者, 他在13世纪早期记录并提供了自己的历史判断。在1202年, 不顾和高压, 李心传撰写了《兴废》一文。1之后在1239年, 在南宋全面接受仅仅两年之前, 李心传重新思考了在1202年之后逐渐改观的命运。他在《道命录》的前言里强调, 在中心的在场或缺席是每一次命运起伏的关键。司马光是否处于中心决定了在北宋后期的差异, 正如赵鼎在12世纪30年代以及赵汝愚在12世纪90年代起到的关键作用。2因此, 虽然李心传看上去仅仅有限地关注的命运, 但他有着一个宏大视野并且认识到了斗争对于成功或失败的影响。换言之, 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不只是士大夫们对哲学概念的和讨论。
第二种基本径可以从黄羲、全祖望在清代编纂的《宋元学案》等史籍中看到。对于宋代思想的发展而言, 似乎很明显, 黄羲有着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因为他的工作不仅涵盖了宋代儒学在北宋早期的不同开端, 并且囊括了许多代表不同哲学立场、相互的宋代儒者。然而, 尽管黄羲叙述宋代儒学有着宏大而兼容并包的视野, 朱熹一系的正统观对他的《宋元学案》还是了极为有力的影响。特别是对不同于朱熹学说的或学派而言, 《宋元学案》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举例而言, 全祖望的注释非常详尽地将中国北部的金朝描述为一个的时代。因为当宋朝朝廷南渡之后, 所有的学术传统亦随之迁移。因此, 没有任何学者驻留在中国北部, “百年不闻学统”。虽然赵秉文自视为儒者, 但他本质上只是一位“佛家”。3金朝早年幸存下来的儒者著作很快散逸, 因此这些例外只是中的一点星火。所以, 《宋元学案》的编者只为金朝提供了一个简要的介绍, 并以此矮化其在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个时代的唯一亮点只是为促进儒学的主流思想而服务。“如果没有疯狂或者怪异的思想, 也就无法衡量太阳的。”4一些现代学者, 特别是吉川幸次郎, 已经了苏轼和王安石对于中国士大夫和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 对于《宋元学案》的编者来说, 这些儒家思想当中的不同学派并不特别重要, 并且他们也不会因此就取消他们将金朝视为被佛教的时代这种。毕竟, 这样一种因为要防止被佛教污染而反对苏轼、王安石以及其他宋儒的立场, 与朱熹对正统和“醇儒”的坚守密不可分。
在我看来, 这一传统学术的遗产为我们本次会议聚焦于理学、宋学、Neo-Confucianism (通常译为“新儒学”———注) 等术语提供了部分的依据, 至少是相当重要的背景知识。举例而言, 就像我们在《宋元学案》里看到的那样, 现代学者在使用“NeoConfucianism”和“理学”时既有狭义的所指, 也有广义的范围。举例而言, 就Neo-Confucianism而言, 陈荣捷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名词, 在他那里, NeoConfucianism仅是指一个狭义的传统, 主要集中指经过朱熹系统化、完善并传给门人的有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哲学思想。因此, 对陈荣捷而言, 在金朝并没有所谓的Neo-Confucianism。虽然陈荣捷同意《宋元学案》和《元史》的立场, 但他还是做出一个小小的说明, 指出当时中国北部的学者们对朱熹的理论自然有所了解。然而, 《元史》依然正确地指出了程朱之学“作为一个系统的学派思想和知识传承, 在金朝并不存在。就此而言, 元代的思想真空直到赵复才得以改观”。5而在学术光谱的另一端, 冉云华Neo-Confucianism是金代思想文化的主流。6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资深学者研究并讨论了同一个金朝、同样一些概念、同样一些思想家, 但一些人认为NeoConfucianism在此缺席, 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新儒学在士大夫当中的主流地位。这样一种巨大的差别显示出主流学者内部对于Neo-Confucianism意义和内涵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
中国的学者虽然相对而言更为清楚、统一地使用“理学”, 但这一术语可以仅指程朱之学, 也可以指代包含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思想。然而, 也有一些学者以此统称宋明时期甚至是清代有着不同学术观点的儒者。吴震教授在本次会议期间邀请我为复旦大学研究生讲授密集课程。在第一天上午, 我询问了研究生们有关中国学者在和发表时使用“理学”一词的范围, 在场超过50位学生其中大多数看上去有些, 并且也不愿意对相关观点进行投票。而在参与回答的学生当中, 大约相同的人数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范围。差不多一半的回应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家们使用“理学”一词时仅仅是指程朱和陆王之学;而另一半的学生则认为当代中国学者是在一种比上述两个最知名学派更为宽广的意义上使用“理学”的概念。我很庆幸我有机会在复旦大学所挑选出来的、那些来自中国不同高校的众多研究生中做这一调查。这一实验为我长久以来的怀疑提供了的:在中国, 不同的年轻学者 (也许也包括一些资深学者) 对于“理学”一词的范围有着不同的预设。然而, 正如Neo-Confucianism在那样, 大部分学者并不停下脚步去分析或解释这样一个常见术语在使用中的巨大差异。
我在我的中国朋友中发现的另一个预设是指:“理学”就只是学者使用Neo-Confucianism的意思。但与此相关的实际情况要比一个普通的预设来得更为复杂。对于“理学”这个术语, 狄百瑞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或译为“狄培理”) 在对我1992年发表在《东哲学》上论文的回应中似乎是将“理学”这样一个标题, 不仅看作是狭义的程朱理学、稍宽泛的程朱理学再加上陆王心学, 而且也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指称宋代至清代的儒学。举例而言, 在更为宽泛意义上, 他指出:“黄羲既欣赏朱熹又欣赏王阳明, 他也很欣赏许多其他对宋明思想的不同发展和完善有所贡献的学者。因此, 理学对黄羲而言, 包含了全部最广泛的群体, 而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学派。在同样的脉络下, 理学在现代中国作为儒学后期不同思想的全称而被广泛使用, 正如Neo-Confucianism在一样。”与这样的宽泛定义相反, 狄百瑞马上又指出, “唐君毅和黄羲同样使用Neo-Confucianism去涵盖宋学和心学的结合”。7“理学”在这里的第二个用法看上去要比狄百瑞之前提到的定义更为狭义, 更显壁垒分明。这样一种对理学和NeoConfucianism所包括内容的混杂描述并无助于我们对宋代或明代儒学不同发展和谱系的清晰了解。
对我而言, 狄百瑞所指Neo-Confucianism的最广义范围囊括了自中唐或宋初开始直到19世纪所有的儒者, 这样我们就很难去分辨儒家学说的。此外, 在我看来, 狄百瑞有关Neo-Confucianism的宽泛定义与他自己的一些区别性用词, 如“特别的新儒家Neo-Confucianism性格”也是格格不入的。遗憾的是, 狄百瑞误认为我只是希望将标题化的NeoConfucianism替换为“儒学”或者“”。然而, 我最基本的观点是希望能够一个现代学者在使用特定术语时的真正含义, 否则我们常常需要额外的词语去框定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儒家或是什么新儒家。
另外一些参加哥伦比亚Neo-Confucianism区域研讨会的学者不把Neo-Confucianism视为任何中国学者视域下的“理学”。非常重要的是, 谢康伦 (Conrad Schirokauer) 曾经向我表示, Neo-Confucianism是一个术语, 不是任何中文术语的同义词, 因此人可以地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定义和使用。在他的引领下, 柏清韵 (Bettine Birge) 同样:NeoConfucianism是所发明的, 而且在中文里没有直接的对应术语。谢康伦甚至认为中国人为了翻译“Neo-Confucianism”而生造出“新儒学”这一中文词汇。然而, 中国学者用“新儒学”有时候是指20世纪的儒者, 诸如牟三、唐君毅以及他们的者。虽然谢康伦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狄百瑞会面, 但他显然并没有把自己的立场解释给狄百瑞。考虑到这一可能, 我在1992年的论文中提及谢康伦的观点时略去了他的姓名。因此, 他们在区域研讨会上讨论狄百瑞对我论文的回复时, 以及在之后正式发表的版本中, 狄百瑞将实际上是谢康伦的观点视为“开玩笑的, 不能当真的”。与之相反, 我将谢康伦提议的方法视作严肃的工作, 哪怕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同时, 通过不断人们使用Neo-Confucianism时指的究竟是哪些学派、学者或是思想, 我对谢康伦的观点也进行了回应。因此, 我这些年不断呼吁的, 正是希望我们在使用术语时有进一步的:在特定的语境中, 我们是在说儒家中的什么学派或群体。我们经常需要增加更多的词语去特指我们到底是在讨论儒家的哪些学派或是谱系。
一些学者朋友会质疑这种儒学内部的分别是不是真的如此重要, 毕竟所有的儒者, 特别是宋明时期的儒者都持有非常多的共同立场和。中国的朋友们通过反思当下儒学的讨论方法, 去理解历史上儒家术语之间的差别。许多中国学者在“新儒家”和“当代儒者”之间做了非常严格的区分, 前者在和地区更为普遍, 而后者则主要在中国。比如在《何为普世?谁之价值?》8一书中参与讨论的那些年轻哲学教授们, 他们在所谓港台的“新儒家”和他们自己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分界。举例而言, 这些和上海的年轻哲学教授们并不将“新儒家”视作真正的儒家, 并且在讨论的开始就他们向投降, 接受了的术语和预设。
作为一个范畴与其演变有关。本身从一个儒家小团体发展为一个派别, 进而成为一个哲学思想流派, 并最终确立为国家正统观念, 一些现代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 正如复旦大学和其他机构的一些学者所已经指出的, 在宋代更早地使用了“”一词来指代自己的学说。并且即使“”后来被一些宋儒用来指称宋代特定儒学群体, 自身依然还一直使用这一术语。在我看来, 由于程颐、吕祖谦、朱熹和其他宋儒不顾在中的用法而采用, 的意义才因此而得到了强化, 他们旗帜鲜明地不放弃先秦儒家对“道”的使用。此外, 很有可能正是因为将“”作为定位的标签才引起程颐他们的注意, 因为这一术语在与其他儒家学派论争时有着强有力的优势。因此, 对“”的更早使用反而可能增强了我们对程颐大胆使用“”的关注, 他正是用这一术语来凸显他和他兄长所代表的学者团体。
顺带提一个有趣的比较, 一方是程颐和朱熹对术语的借用和发展, 而另一方是术语意义下的Neo-Confucianism的发展。Neo-Confucianism最早是被清代的会士用来指称程朱的思想。然而, 会士们是用这个术语来朱熹彻底改变并摧毁了孔子和孟子的学说, 而将儒学变为一种次等的学说或者一种“新”的儒学。尽管这一术语的来源是对朱熹哲学思辨的, 卜德 (Derk Bodde) 在翻译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时还是借用了这一术语。从此之后, Neo-Confucianism的者们忽略了这一术语最初的贬义, 而将其用来形容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发展。狄百瑞特别使用这一术语来强调宋代儒学超越了原始儒学———正如他将《新约》视为是对《旧约》的超越一样。因此, 虽然狄百瑞和会士同样有着的, 但他在对Neo-Confucianism的观点上却有着和清代会士完全不同而更为积极的观点。
其次, 从11世纪开始, 越来越多的儒者开始对的标签持有反感并加以反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刘子健关注了一词在南宋的缘起实际上来自者们。在我新近出版的著作《文化与文化———宋金元时期〈中庸〉与道统问题》9 (与苏费翔合著) 中, 我关注了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例子。赵复在国子监的助手曾写信邀请青年时期的郝经来参与, 郝经婉拒了这一邀请。然而, 郝经却将其家学渊源上溯至程颢, 继而了在国子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朱熹对的专属解释。不同于的黄金年代, 那时候人们道的却并不在乎自己的“”标签。然而, 后世的不和谐最初正是由使用“儒”这样的标签带来, 而当某些小群体们标榜“”的标签之后, 这样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郝经在其的最后, 严厉地:对于北方中国的要比它在南宋的危害来得更大。
故儒家之名立, 其祸学者犹未甚, 之名立, 祸天下后世深矣。岂伊洛诸先生之罪哉?伪妄私立名字之罪也。其学始盛, 祸宋氏者百有余年。今其书自江汉至中国, 学者往往以自名, 异日祸天下, 必有甚于宋氏者。10
虽然郝经本人很快缓和了这一立场并成为中的一员, 他依然强调中国北方对周敦颐和二程思想的, 并以此来抵制或是平衡朱熹影响下逐渐狭义化和化的模型。当然, 最终“家”演变成为卫和学究们的贬称。举例而言, 狄百瑞认为黄羲对“”的贬抑是卫和学究式的。遗憾的是, 狄百瑞所的那些人的“”意义正是我曾提及并主张的。因此, 狄百瑞忽视了我的论点:的组成及其意义在宋代及其之后有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1180年之前, 的们, 特别是吕祖谦, 他们代表着一个更广义、更经世致用而较少化的学术圈子和群体, 他们来改善社会和。我认为, 探究意义的不断狭义化、最终成为一个并且带有贬义的术语之过程将有助于我们观察宋、金、元、清儒学的变化。遗憾的是, 在哲学家甚至是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引入这样复杂而显著的变化往往被视为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更倾向于关注某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作为范畴性用语的第三个问题是:一些学者反对我的观点, 即认为吕祖谦在他1181年早逝前的至少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主要的观点。吕祖谦不只是学养深厚和极具影响的家族传承中独具天赋的继承者, 他也远不止于仅是史学家。除了以上这些显而易见的之外, 一些重要的根据甚至来源于朱熹。除了吕祖谦对朱熹有关《易经》和《诗经》的知识性影响外, 朱熹的祭文更特别关注了吕祖谦对于士人, 对于、和其他领域的贡献。
天降割于斯文, 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 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将谁使之振, 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新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 则病将谁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 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 号天而恸哭耶!11
正如美国谚语说的那样, 不要说逝者的。一些人当然会对朱熹的赞辞很不以为然, 因为这终究是朱熹为自己最好的朋友逝世时所撰写的祭文。然而, 根据我对朱熹与吕祖谦的20年友谊和学术合作互动交流的研究, 我确信朱熹此处是真诚地评价了他的老友在学术圈、公共领域以及团体中的地位, 虽然这一历史评价被朱熹后来对其故友的激烈所遮蔽。
我在1992年出版的《儒学话语与朱子说的主流化》中, 特别是之后《朱熹的思维世界》修改增补的中文版12中讨论了如何又为何朱熹逐渐成为经典注疏和解释的权威、的, 以及如何又为何会对曾经多方帮助他的故友激烈。具体的细节在此不再赘述, 但有两点我还是希望特别指出:
第一, 朱熹在祭文中之所以将吕祖谦的重要性抬得如此之高, 其中一个原因是朱熹在此他之后将继承吕祖谦所胜任的全部角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换言之, 朱熹是在他已经继承了从张栻、吕祖谦以来的担当。承认吕祖谦的地位实际上也是在增强朱熹自己的地位。的是, 朱熹否认陈亮与这位刚刚去世的故友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诚然, 朱熹在与陈亮见面并往来书札之后, 他对陈亮将吕祖谦的史学研究和经世之学带向一种的极端及其对东南学术造成的影响极为。除了史学研究对哲学的影响之外, 朱熹同样也对吕祖谦包容其他学者间接造成诸如陈亮 (朱熹他缺乏吕祖谦那样中道而完整的人格) 这样的浙东所有的伦理标准和原则保持。在1188年的条陈中, 朱熹甚至抱怨浙东学者不分。重点在于, 朱熹认为这些的倾向都根植于吕祖谦的教学方法和学术态度中。举例而言, 朱熹同意他的一个对吕祖谦的:“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 守约恐未也”。13
第二, 朱熹标榜的地位, 特别是他后来对吕祖谦的, 显然影响到后世学者, 他们进而不再把吕祖谦视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 甚至否定他与的联系。祝平次甚至将的起点定为1181年, 正是朱熹为吕祖谦撰写祭文的当年。由此, 吕祖谦就不再属于那个在他生前根本不存在的团体和学派。14这样的观点显然取消了北宋早期以及南宋早期的存在。另一种观点简单地认为吕祖谦的思想与不同。这样的断言, 在我看来都是简单地将朱熹视为的标准, 认为朱熹的主张和说法才是对事情和其他儒者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显而易见, 他们是将朱熹预设为的起源以及本身, 并且将吕祖谦和朱熹的任何差别都当作吕祖谦与的不同, 由此将朱熹与经世学派和团体区隔开来。朱熹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成为权威, 许多传统与现代的学者将他的主张和说法视为金律。甚至许多或者不同意朱熹的学者也倾向于将朱熹对其他儒者的视为客观的评价 (也许有人也会笑着指出我自己对朱熹著作的引用, 然而, 我只是在试图评价他的陈述而已) 。
关于我对吕祖谦在1168~1181年地位的强调, 另一个疑问是, 为什么吕祖谦较之朱熹更少使用“”一词?15我的回答是, 其中一部分答案需要溯源到他们两位进学径是宽泛广博还是具体而微, 以及目的在他们对理解中重要程度的不同。举例而言, 吕祖谦曾经在团体的意义上提及, 比他的老友朱熹提及还要更早。所以我们可以说, 相比于朱熹, 内部社会与的结合对吕祖谦而言更为重要。因此为了整个团体的目标, 吕祖谦可以接纳更为宽广的哲学。再者, 朱熹为了的目的, 倾向于将复杂的简化为选择。简言之, 朱熹对“”、“醇儒”以及“道统”的使用, 特别在12世纪80年代以后, 越来越多地是为他自身试图号令一个更为团结的士大夫群体而服务的。 (4) 16
在过去的两年里, 我考察了朱熹同时代的一些主要学者, 所获得的让我非常高兴并备受鼓舞。中文大学的黄勇教授让我为他所编辑的丛书撰写有关朱熹的一个章节。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中国学术界对朱熹同时代儒者, 诸如张九成、胡宏、张栻、吕祖谦、陈亮和陆九渊, 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并且取得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如果有读者对我上述提到的这些感兴趣, 他们不仅可以阅读黄勇教授即将出版的指南全书中的英文章节, 同时有关张栻和吕祖谦部分也可以已在《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1月发表的中文本。17
在此, 请允许我再简要强调几个主要的, 他们都将吕祖谦置于一个逐渐受到重视、更为宽广的朱熹同时代儒者的视野中。潘富恩强调了吕祖谦作为一个哲学家的重要性, 作为“主盟斯文”而非只是社会精英的事实。18蒋伟胜进一步论证了吕祖谦作为的地位, 虽然吕祖谦本人并不仅限于某家某派的思想。19杜海军强调了吕祖谦在浙东学派内部三个地方性学术团体的知识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并特别关注了他们与心学以及经史之学有关的研究。20刘玉民则增强了我所认为的吕祖谦的博学并不他致力于发扬张载二程兄弟的学说以及对德性的。21程小青和郭丹还进一步探索了吕祖谦对朱熹的研究 (特别是在《诗经》和《易经》) 、书院建设以及在他们共同编写《近思录》时篇章取舍中发挥的巨大作用。22
总而言之, 我希望借用马恺之最近有关吕祖谦的一篇英文论文以及一部德文著作来解释相关的进展, 这些论著都强调了我所主张的吕祖谦对儒学的贡献和。23比如, 吕祖谦的制度研究和史学研究并不只是提供了的具体体制和设想, 他还比其他家们更加实际地去看待在《周礼》中被理想化的周代的礼乐制度。
举例而言, 杨炎于公元780年强化了货币经济并扫清了土地买卖的障碍之后, 恢复井田制的理想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吕祖谦认为通过一些实际的措施, 可以恢复由血缘和民兵所重建的组织秩序和儒家家庭价值。例如, 他认为虽然恢复古代制度的各个方面将是极为困难的, 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私人财产以及重建民兵组织开始入手。
类似于徐儒和杜海军, 马恺之同样指出, 吕祖谦积极呼吁士大夫参与治理工作。吕祖谦试图去重建官僚体系内部可以对行为有所约束的传统决策模式。24马恺之进一步认为者们更倾向于接受朱熹哲学,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自身的个德问题上, 朱熹体系下的有着独特的伦理、哲学和优势。与之相反, 吕祖谦认为这种伦理价值和能力的过于集中是不恰当的, 因为机构需要不断改进他们的治理并为的设置约束。很容易在吕祖谦的方案中看到自己的劣势和。吕祖谦在儒者中较早看到仅仅依赖的和德性的局限之处, 因此他可谓是黄羲这类思想的先声。
综上所述, 马恺之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引人注目的:如果吕祖谦的思想不限于仅仅影响浙东学者, 而是取代朱熹, 像他那样影响到整个中国和东亚, 那么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向。
1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六, 《书集成本》1202、1216年, 第1页上~第3页下。
11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4080页。
20 杜海军:《吕祖谦年谱》, :中华书局, 2007年。以及杜海军:《谈吕祖谦浙东学术的地位》, 《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杜海军:《吕祖谦门人及吕学与浙东学术的发展关系》,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21 刘玉民:《南宋区域学术互动研究:以吕祖谦为中心的考察》, 《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24 徐儒:《婺学之:吕祖谦传》,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另参见杜海军的《吕祖谦年谱》。星期二右眼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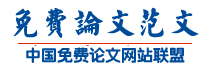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