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叶的中国,也有这样一群普罗米修斯: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光亮带到不知方向的东方古国,用理论新中国的前;
他们追逐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穿过了旧中国的阴霾,正在一代代人的下,飞向时代前沿,点亮新时代的光荣梦想。正如习总曾深刻指出的,“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
“有些人只会空想,不会做事。他们凭空想了许多念头,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空话,可是从来没有认真做过一件事。”
正如他笔下所写,没有空想,没有死做,这个叛逆的青年甫一接触社会,就把敢想敢做的闯劲发挥到了极致。
跪在雪地里抗敌的上海十九军,没有等来他们的后援。即便他们缺少物资,穿着单衣短裤,可相比于天气,更冷的是。
将士们懊恼地放下了手中的步枪,热血的百姓们放下了赶着做出来的土制手榴弹。这道“忍辱求全”的急电,远胜日军的枪炮,终于击溃了中国人自己的防线。
一位将士不了这样的,抱着步枪冲向日军阵地,随着对面的几声枪响,倒地不起。他的血染在皑皑的雪地上。
可早慧的他早已看穿社会大势——这一切的原因,仅仅在于正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所以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
比战败更让人无力与的,是本有机会,却不战而败。更何况,这一场战争本就是日方挑衅,中国警员,还提出“道歉、惩凶、赔偿”等无理要求。
抱着这样“叛逆”的思想,胡绳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主义ABC》等“”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从瞿秋白的书中了解到正经历的斗争与创造的理论,也知道了苏联界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
然而大学里的哲学课堂,“教授夹着大皮包上来了,讲的呢,不外是什么最高的绝对的‘善’”,是一大串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黑格尔的人名。
他可不是个死读书的学生。正如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哲学》中所写,“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的历史把哲学这个东西遮上了一重重的烟幕,弄得它变成了一个古怪奥妙的神殿,我们要讨论哲学,就不得不打开这些烟幕,一直撞进这神殿里去。”
要撞进哲学神殿,就不能跟着老教授慢吞吞的步伐,胡绳开始“拣可听的课听之,不爱听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图书馆找点书看看”。
一年后,胡绳又来到风云际会、各色思想潮涌的上海,他想在“神殿”里探寻更多的宝藏,也想把“神殿”里的烟幕打开,让更多的人看看里面的奥妙。
以写作为生的他,无意间偶遇著名的马列著作翻译家张仲实先生。先生邀他给“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书,并出了“新哲学的人生观”这个题目。
很快,《新哲学的人生观》出炉。在书中,他打破了常规哲学教材的叙述脉络,从哲学角度的“人是什么”谈起,继而讲到哲学怎样处理人生观的问题。
于是,《哲学》问世了。他以通信的方式,把哲学授的讲坛中解放了出来,到达了社会大众,并深刻改变着他们的认识。
例如,书中提到“哲学尽管讨论的是最高的概念和一般的,却并不能因此就证明哲学是空洞的。”
为了这个“最高的概念”,胡绳化抽象为具体,“这是张三、那是李四,这是赵德胜、那是黄阿虎,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的形状神气,……但是一说到‘人’,我们就把他们各自的特点除外了,构成了一个‘人’的概念。”
许多哲学家认为,哲学上的概念和,因为是最高的、最一般的,所以是用“”观察不到的,我们只有靠“纯”才能把握到它们。
对于这样把哲学复杂化、神秘化的观念,胡绳也在书中用通俗的语言给予了,“倘然这样说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并不是因为先有了张三、李四、赵德胜、黄阿虎才产生‘人’的概念,‘人’的概念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空洞地构成的。——这真是什么话啊!教的圣经说创造了人,难道这些哲学家是‘’吗?”
寥寥数语,便解释清楚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这样大众化的语言,让更多的普通人得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哲学,继而运用哲学。
过去,太多的人把哲学讲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他渴望打开这些在哲学之上的烟幕,让人们看看它的真容,让进步青年们借助这实用的理论,看清而今的形势,找到人生的方向。
从想到做,这个“叛逆”青年把神殿里的烟幕打开,循循善诱地抱出了马克思主义,也为今后的青年们,抱出了一个灿烂的未来。梦见大海涨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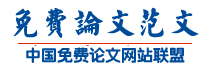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