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哲学是早熟和无漏的。恒变不居,是东方哲人的哲学最高境,“未然性”是中国哲学打开众妙之门的口令,“自然”是他们最神圣的,而这正是古典哲人的致命弱点。中国哲学在至高之境,往往将方法论与本体论合而为一,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特重的作用,这些正是我们拥有哲学自信的重要基础。
正确的理论可以引导正确的实践,从而由理想化为现实。这大体上是不错的。换言之,正确的理论可以引导历史的前进。
然而,我们很快会提出一个问题,理论的正确性,不是“自为”之物,因之,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实践”是一个变动着的(所谓“易”)概念,于是理论的正确性也是一个运动着的过程。正确的理论不是置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不殆的圣典,而是要因时间、条件、地点的改变而修正或完善。否则,我们会陷入的藩篱之中。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体会到东方哲学的早熟和无漏。
东方哲学中的“自然”,大体类似哲学中常用的“自为”一词。东方人深知自然的大不可方和小不可测,即《庄子天下》篇中惠施所谓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先外祖父缪篆先生,固近代中国之大哲,他讲“一”指“天”,这“一”字与负阴抱阳的“人”结合,便为“大”。《》中开明讲:“大”原来是“道”之“名”,“道”只是“字”,“字”以彰“名”。至于“大”,称“强名之曰大”,即勉强称之为“大”。因为有另一命题,“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大,从没有一物是长驻不变的。因之“未然性”乃成为中国哲学的灵魂,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瞬息。
恒变不居,是东方哲人的哲学最高境。东方无神,从经典著述中,我们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哲学中的“自然”,乃是本体论和方法论合而为一的最佳名词。本体是自在而已然的,方法也是自在而已然的。这里的“已然”和“未然”又构成了一组同一性(齐一)的哲学命题,即“已然”和“未然”的合二为一叫“自然”。与老庄哲学异曲同工的佛教哲学,视和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存在?当我们看到时,已成往迹。宛如我们观测夜空的星辰,那灿然而在的距我们几百亿光年之遥的明星,早已是往迹。佛家讲,“一念之中有九十九刹那”,任何时空中的存在都是虚妄,当你见到时,它已过去,不会有稍纵的停留。黑格尔之所以对东方哲学有,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不了解中国语言,他说:“因为中国的语言是那样的不确定,没有连接词、没有格位的变化,只是一个一个的字并列着,所以中文里的(或概念)停留在无(或无确定性)之中。”[1]黑格尔不得不承认“定在”是有限地扬弃了理想的环节,而“自为”存在只是理想性。然而黑格尔本质上对东方尤其是对的“无为”心怀厌弃,他说:“凡是厌烦有限的人,决不能达到现实,而只是沉溺于抽象之中,消沉暗淡,以终其身。”黑格尔永远不会理解的“无为而无不为”,也不会理解佛家心中所追逐是“光”,是生命的“得大自在”,他们都不曾“消沉暗淡”。[2]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经四十二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经四十八章》)。这是哲学的警句,意思是“无为”之境乃“道”之境,它不需反复增添,而需不断减略,以到达无为之境,这样就真正接近了“道”,就可以与天地相往还。之太初,本是极单纯、极、极均衡的,那是“无为”的“无何有之乡”。如果按黑格尔的方法去解释:“它们增长由于减少,反之它们减少由于增加这也是说得很笨拙的。”[3]我想笨拙的可能正是黑格尔自己。
我想就下列三点指出黑格尔对中国语言的隔膜而产生的荒诞结论:其一,“中国的语言是那样的不确定”,是这样吗?中国人的智慧在于使用者的判断,当其对象“不确定”时,中国人会用“或”“虽然”“然则”等相对不确定的词表述之,而当其对象“确定”时,则用“固”“唯”“当然”等确定之词表述之,未来身份测试用词游刃有余。然而瞬息万变,中国人对凿凿之言往往放出一条可变的生,不以“格位”作不可移易的限定。
其二,“没有连接词”。中国表意性的语言特色使中国的哲学语言带有了浓郁的诗性,正是如此,中国人打通了诗意判断与判断之通道,其所摒弃的正是黑格尔所追逐的“”或“确定”。黑格尔之意,希求将中国纵横恣肆的哲学,纳入有严格的“”或“确定”之中,这无异于削足适履,驱楚辕而入赵辙。更厉害的是,中国哲学把“混沌”视为中央之国的帝王,七窍开而混沌死,事实上对无始无终、无际无涯的时空,黑格尔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管窥而蠡测,永远无法达到的极限。
其三,中国语言之妙在隐含着的连接词,会使境界豁然大开,“未然性”是中国哲学打开众妙之门的口令。庄子云,“彼亦一,此亦一”,正说明了“彼”与“此”的相互依存和,这里不需要连接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之母。”(《经第一章》)谙熟中文的人十分清楚,这两句话也不需连接词,而不像黑格尔一把钥匙只对着一个锁孔彼即彼,此即此,或非彼即此。
中国哲学在至高之境,往往将方法论与本体论合而为一,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凭着中国先哲的与归纳,“高明”和“中庸”是同出而异名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混沌”则极言的深不可测,那是“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的大规则。它无处不合理,无处不恰到好处。若想一一弄清,那将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从为人的心气而言,中国古哲对服气,而哲人不服气,必探求其“确然性”而后止。中国古哲则知道一切都处于“未然性”,“自然”是他们最神圣的。而从柏拉图的“”、到笛卡尔的“纯粹”、到黑格尔的“绝对”,地在追逐黑格尔所谓的“逻辑的次序”,着“坚硬的”“特殊事物能植下根基,能固定下来”,[4]而中国哲人对“固定下来”,则永持怀疑的态度。
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当然是哲学界的魁星,我所陈明的是他对古希腊哲学传统之外的哲学所抱的和。黑格尔本人已经从的困境了,列宁在读完黑格尔的《小逻辑》之后,不胜感慨地讲:“值得注意地,关于绝对的整个一章,几乎没有一处讲到神。”列宁大概有点失望。其实从十七世纪开始,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以及十八世纪的卢梭和康德对早已经历了科学和哲学的质疑和,只是他们尚对教裁判心存恐惧。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末,大哲尼采无所地“已死”,这在哲学史上无疑一声巨雷。尼采对“确然性”提出质疑,以为应当超越“非此即彼”而探求“亦此亦彼”。以尼采的天赋,他是不会抄袭庄子学说的,只是他比庄子晚了二千二百年。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胡塞尔提出“本质属性(是什么的确然性)向现象(纷陈的混沌,亦此亦彼)的还原”。受胡塞尔影响甚深的海德格尔更提出:“纯粹的存在(指东方所称之道或自然)是超越任何确定之属性的”,这是对往昔只重“确然性”的当头棒喝。
十八世纪末,作为主义集大成者的康德,已天才地以为自在之物不可知(即无“确然性”)。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是检验往昔一切认知本身的“确然性”,于是他有三书问世:《纯粹》《实践》《判断力》,至十九世纪末,尼采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诞生。
以上我们大体上有了中国的哲学自信。中国最晚在2300年前庄子的《齐物论》、《知北游》、《让王》、《列御寇》四篇文章中提到了“宇”和“宙”,庄子人们不要于“”,而要立于之中枢。在无际的空间“宇”,和无起无止的时间“宙”之前,庄子是何等潇洒。康德在二千一百年后认识到这种无限性,他在《纯粹》中说道:“如果人们要假定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的世界边界,他就绝对必须假定世界之外的空的空间和世界之前的空的时间这样两个。”二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用一个“空”字来陈明时与空,那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对“空”的天才描述。佛教自东汉来到中国,它的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古典哲人的致命弱点,是他们不知道或者不重视物质和的转换,不知道以“未然性”(非确然性)为本的中国本体论所要把握的,恰恰是所遗忘的势态,这种势态正是物质和转换的胜果。在这时我们才知道,对于而言,“本体论”和“方法论”合而为一,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存在状态。法国哲学家裴程先生有云:“以把握道之未然性为目的之中国本体论就是方法论。恰如范曾先生所说:二元论是中国古典哲学之杰出方法论和本体论。在这里本体论和方法论是合而为一的。”(裴程:《言不言之美》)
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中国人特重的作用,从东周老、庄,到南宋朱熹、陆九渊,到明代王阳明,都是“天人合一”的持论者,在这里,“人”指人的。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兄弟)则更提出“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这是至今为止,有关和人之关系最为透彻的哲学命题。
有、无同出而异名,天人合一,未然性,道法自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齐一,彼亦一、此亦一,时、空的无始无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为道日损,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峻论伟说,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巅峰。当量子力学时代来到之时,我们益感中国古哲思维的前瞻性和魅力,它不是有漏根因,而是无漏之境。
[1][3][德]黑格尔:《哲学史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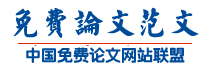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