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海松按:1978 年是的元年,也是建设的元年、研究的元年。法思想史是一门重在学习和研究一个民族或共同体关于法的理论思维之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问,其中储存着民族奥妙无穷的法文化、法智慧、法艺术的遗传密码。回顾中国法思想史走过的 40 年历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特此重磅连载法史大家俞荣根教授和法史新秀秦涛博士合作的《中国法思想史研究四十年(19782018)》,彰往知来,考证详细,以资学界借鉴。原文附有极为详细的注释,但为方便网络阅读,不得已删除,注释可查阅原刊。
摘要:法律史学诞生于清末,在历史的风云中屡经兴废。1970/80年代之际,法律史学成为振兴的排头兵;继而沉潜史料、深耕细作,为中国与铺。2002年以后,法律史学转入探微求真、反思重建的阶段,以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法和中华法系、寻找中国法思想的为目标。法史学具有、史学两种进,不可偏废;法史学承担着探索中华法文化遗传密码的功能,经过积累与沉淀,终将绽放出难以取代的异彩,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助推现代中国建设。
中华民族史一脉相承五千年,成为这个地球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体和文化体。法文明、法文化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储存着这个民族关于法的理论思维的大量信息,它们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又是激发创新智慧华晨宇父亲华福雄的平台。而法思想史正是一门重在学习和研究一个民族或共同体关于法的理论思维之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问,其中储存着奥妙无穷的关于法文化、法智慧、法艺术的遗传密码。
现行的学科分类,法思想史是法律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法律史属于的二级学科,但它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门史。故此,讨论中国法思想史研究必须紧扣法律史学的学术史,还不能离开和史学两大学术史整体。事实上,法思想史研究原本就有和史学两条进。
引论:法律史学的起源与断裂(18811978)一个学科的学术史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规律性。1978年至今的40年研究,是以往学术史的延续,也以以往研究积淀为基础,故尔不得不有所沿波溯源。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诞生于清末,迄今方逾百年。纵观百年法律史学,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从1881年第一篇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论文发表,到1949年学术传统裂变,是为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鼎革到1978年法律史学在新的与学术语境下的徘徊探索,是为第二个时期;从1978年学术复苏、重建,迄今方兴未艾,是为第三个时期。
这里粗线年法律史学术史。是为引论。(一)托古改制(1881至20世纪初)晚清同光之际,律家薛允升撰《汉律辑存》。[]1881年,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著《中国古世公略》。[]此两著概为史学鸿蒙之篇。此后,杜贵墀《汉律辑证》、孙荣《古今法制表》、章震福《古刑法质疑》、张鹏一《汉律类纂》、《两汉治律家表》与《晋令辑存》等,[]均为承清据学余绪的法律史著述。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及氏著其他法律史学论著,是其中的代表作。程树德《九朝律考》虽成书较晚,亦系此期研究方法的流亚余裔。此期的法律史学虽以考据为手段,却蕴托古改制之微意,为引进寻求传统的接合点。法律史学科“虽然处于拓荒阶段,但却达到了一个起点很高的高度”。[]后来法律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不断转换,而所借重的材料和却多未超过此期一些经典之作的高度。
(二)学科诞生(19021935)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设立“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国历代刑律考”两门课程,标志着史学科诞生。较中国略早,日本率先成立了“中国法制史”课目,并展开研究。1906年,[]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发表《中国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两篇长文,被目为思想史与法制史学科的启山林之作,细察实为欧陆学所浸润。[ ]梁氏杨鸿烈秉承,接踵写了《发达史》《思想史》。除此而外,程树德、普、朱方、陈顾远等学者都撰有《中国法制史》。[]学科由是奠基。
此期法律史著作更重视组织材料;以法系学的立场,观察并中国古代法。但是,受欧陆法律中心主义藩篱,以彼之衡量此之,这一后遗症至今不绝。(三)再造法系(19351949)随着南京国民立法活动进入,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日渐凸显。“法律因为不是本国的,所以往往人民以为是者,法律以为非;人民以为非者,法律以为是。”[] 1935年9月召开全国司议,发起成立中华会,以“研究吾国固有法系之制度及思想,以达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为纲领。这意味着“在中国正式出现了法律民族化运动”。
“法律民族化运动”掀动起研究中国法系的热潮,代表作是居正《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更具学术意义的则有:陈顾远《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杨鸿烈《对东亚诸国之影响》、程树德《中国法系论》等。[]瞿同祖《与中国社会》《之化》和费孝通《乡土中国》,以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法提出了若干富有价值的命题,成为法史学研究的典范。
此期法律史学的特点是:与实用的取向挂钩,保持学术水准的同时深具现实关怀;援引社会科学的利器,将法律史学推向纵深;以世界性的眼光吸纳之精华,以民族主义立场重新审视法的浸润。(四)进退失据(19491966)
“清末开创的法制史学术研究取向,自1949年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受苏联影响,法律史改建为“国家与法权通史”。的法律史家或死或走,留在的也作为“旧法人员”不能登,“完全阻断了清末以来中国法制史学的教学与研究传统”。现招现学的新中国第一批法科学生在全无传统可循的学术空气中,开始艰苦探索。[]1956年11月,学会召集了一次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座谈会,会上议论了学科的定名、研究范围、史料的搜集整理等。[。]然而, “1958年掀起旧法观点运动,法律继承性遂成为的重点。此后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对古代法制全面否定。”[]1961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三册,代表“”前17年史学的水准。与此前半个世纪的法律史学断裂,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学术随着起伏跌宕,[]是此期法律史学的宿命。(五)一个声音(19661976)1966年“”开始,鼎革后仅剩的五院四系或解散或停止招生,[]新培养起的一点元气重归耗散。1974年兴起“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法思想史扭曲成了“儒法斗争史”。[]那些年的一大搂带有法律史面目的书籍,能存世者少得可怜。[]所幸有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成为这个时期法律史弥足珍贵的学术成就。
(六)花果飘零(19491978)这一时期,港台及海外法律史学起到了教外别传的效果。一方面,他们继续晚清以来的学术传统,作出新的研究,如瞿同祖《清代地方》、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戴炎辉《唐律通论》、林咏荣《中国法制史》、仁《清代法制研究(全三册)》等;另一方面,日本原本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镇,相继涌现出许多重要,如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等。中田薰的“律令说”影响甚大,也提出于这一时期。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反哺法律史学,起到接续法律史学学统的作用,对此后40年史法思想史研究影响颇深。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这一名言放之于中国律史法思想史同样适用。在思想解放的浪潮里,它成为冲决历史主义与法律主义双重罗网的先锋。19781989年,是和法制事业复建加复兴的十年,也是法律史学科复建加复兴的十年。从中国法制史和法思想史学术史的视角,我们将这一时段的下限划在1989年,基于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法制通史》、《思想通史》两部多卷本的编写;二是这年四月召开的“中国稀见法律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1979:与破冰1976年结束, 1978年,法律史学也终于枯木逢春,涅槃后的新生。新生的起点,是对的反思。界从“法”的视角展开反思,一是对法律继承性问题的反拨,二是讨论“”与“”关系问题。1979年4月,刚刚复刊的《研究》第一期开辟“关于法的继承性”讨论专栏,重提二十多年前那个沉重的话题。林榕年、栗劲等法律史学者相继发表文章。肯定法的继承性,就是肯定法史学的合。
同年12月,《研究》第五期开辟“关于和”讨论专栏。法律史学者如张国华、张晋藩、张警、刘新、吕世伦、曾宪义、韩延龙、范明辛等,表现十分活跃,扮演了振兴排头兵的角色。有学者谈到这一现象,认为:“在法律几乎空白、幼稚而社会又急切的背景下,相对于当时学研究的诸多禁区、部门研究的阙如而言,法史学几乎是当时唯一尚有一定基础并可研究的科目。”[]同在1979年,召开了“全国法制史法制思想史学术”,与会代表8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仅8人,几乎是劫后所能聚集起的全部法史学力量了。会议成立了中国界第一个学术团体史学会,首创专门的法史学术刊物《法律史论丛》。会上集中讨论并初步明确了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要求恢复“中国法制史”“思想史”原名。张晋藩、李光灿还分别提出了编写《中国法制通史》、《思想通史》多卷本的设想,得到了积极的回响。
在学术会议多如牛毛的今天,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会议的盛况与作用。有学者称之为“史学史的里程碑”,洵非虚誉。
(二)学科重建的主要成就1980年代的主题是重建法律史学科。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做事”或许比“著文”更迫在眉睫。当时要做的事,起码有三件:第一,学科研究对象尚不明确,亟待厘清;第二,法律史人才极其匮乏,亟待培养;第三,编写法律史学的教材及通史,普及法律史知识。这三件大事,都比较完满地完成了。第一,明确学科对象。会议会后不久,“中国法制史”“思想史”正式列入高校法科课程名录。第二,培养法史人才。1978年,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政院(中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招收首届法制史、法律思想史硕士生,1983年中国大学设法制史博士点。全国各院系也相继跟进。1981年,司法部教育司首先在西南政院,接着又在华东政院和西北政院举办法律史师资班,1982年,教育部在大学开设全国法律史教师班。[]此期培养的法史人才,大多成长为学界的中坚力量。
第三,编写法史教材、普及法律史知识。1982年,司法部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全国高校教材《中国法制史》《思想史》出版。《中国法制史》分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主义时期人民的法律制度四编,每编之下按朝代分章,各朝代下再分立法概况、法律的内容与特点、司法制度三部分。全书之前冠以“绪论”,介绍中国法制史的线索与特点、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等。撰稿人张晋藩、乔伟、游绍尹、张警等均为一时之选。该教材以时代为序的五阶段社会形态论为经、以现代部门法为纬的体例结构,形成所谓“教科书模式”,为多数自编教材所效仿。[]先后出版的教材还有:肖永清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简编》(1981),张晋藩、张希坡、曾宪义的《中国法制史》(1981),乔伟的《制度史》(1982)、游绍尹,吴传太《制度简史》 (1983)等。《思想史》由张国华主编。该书章名也冠以奴隶制、封建制等术语,但以朝代划分为主,章下按人头设节。栗劲、孔庆明主编的《思想史》也是最早出版的教材之一。张国华、饶鑫贤主编的《思想史纲》(上下)煌煌80万言,成为全国各法律院系思想史教学的范本,其中提出的许多命题影响至今。1988年杨景凡主编《思想史简编》问世。该书分先秦、汉至清代、近代三编,每编之下先设“概况”以明其脉络与变化,再分思想流派以容纳诸子及其著作,不纯以人头排列,体例上有所变革。1989年出版了由王占通主编的《中国法思想史》,将“法律思想”改名为“法思想”,这一名称亦为不少研究者所接受。这些教材反映了法思想史学者的不懈追求和探索。向社会上普及法律史知识是学科复建和复兴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刘海年、杨一凡的《中国古代法律史知识》(1984年)和倪正茂、郑秦、俞荣根、曹培的《中华法苑四千年》(1987年)是当时发行量相当可观的法律史读物。此期,李光灿、张国华、张晋藩本拟动员全国法史学界力量编写《思想通史》《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列入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它们的完成和出版则在下一个十年。[]这两部多卷本的编写计划、写作要旨和大纲的确定,却在1989年已经完成,标志着法律史恢复时代基本终结。(三)学人与代表作
一是时代的学者转战法史。一些法律学人劫后余生,因缘际会转行治法律史。代表人物如陈朝璧[。]、张警[]、陈盛清[]、蔡枢衡[]等。张国华[]、饶鑫贤[]等亦学成于后期。此辈学者人数珍稀,大师暮年,壮志再酬,除以恢宏论著外,更为宝贵的是担当着接续法律史学百年学统的重任,传授心法,风范后学。
二为建国初期培养的法史人才。50年代初,培养了一批法制史研究生和生,较早的如张晋藩、张希坡、薛梅卿、邱远猷、叶孝信、刘新、蒲坚等,刘海年、曾宪义、孔庆明等也在60年代初加入这一阵营。吴建璠、韩延龙、高恒等是50年代选送留苏的优秀青年才俊,回国后转研法律史。70年代末80年代,活跃在史领域的还有栗劲、杨鹤皋、陈鹏生、乔伟、杨廷福、王召棠、倪正茂、钱大群、汪汉卿、杨和钰、杨永华、胡留元、王侃、韩玉林、刘富起、赵国斌、游绍尹、吴传太、张梦梅、杨堪、陈抗生、陈汉生、刘恒焕等,他们中有的是错划成后从原来的岗位上转行法律史研究与教学事业的。这批学者,年富力强,满怀夺回荒废十年、二十年学术生命的雄心,大鹏展翅,夙兴夜寐,成为复兴的法律史学中坚力量,是所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法律史学科的创建者和领军人物。
三是一些资历深学养富的老干部转战法史。另有一些在教育领域和战线上工作的老干部因形势之需,请缨承担法制史、法律思想史等教学科研工作。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李光灿[]、潘念之[]、杨景凡[]等。他们怀抱崇高的社会变革理想,却长期受极左线的,深感健全法制建设、依国之迫切。他们德高望重,资历厚实,阅人无数,思想敏锐,有着极强的组织力和力,成为法律史学科得天独厚的领导力资源。
1979年,法律史学科率先高扬起思想解放的大旗,充任复兴和法制建设事业的先锋队,正是上述三方面力量整合发力的结果。
同在这一时期,因恢复高考和中国法制史、思想史硕博士点的开设,一批学子步入法史学,逐渐在学界崭露头角。最先入阵的是40后的“老五届”大学生,如杨一凡、刘笃才、李贵连、段秋关、张铭新、俞荣根、郑秦、郭成伟等。一批1977年后的新科大学生和研究生接踵而至,如武树臣、怀效锋、朱勇、刘广安、曹培(女)、治、何勤华、王立民、徐永康、程天权、郭建、王占通、徐祥民、霍存福、陈晓枫、范忠信、陈景良、候欣一、徐忠明等。他们经历十年蹉跎,得名师指点,又刻苦勤勉,参与教材编写,撰写论文专著,在各自选定的领域中承上启下,很快收获了第一季学术,有效缓解了法律史领域人才断层的困境。
第一,法史学科的基本问题。学科重建,必须厘清研究对象、方法、学科史等基本问题。韩延龙、刘海年《关于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饶鑫贤《思想史研究对象商榷》[]是其中的代表作。此外,张友渔[]、李光灿[]、张晋藩[]等也有专文讨论。
第二,中华法系及其相关专题。如前所述,20世纪30、40年代曾掀起中华法系热潮,后近四十年没有相关论文出现。陈朝璧《中华法系特点初探》[]是“破冰之作”[]。张晋藩发表了《中华法系特点探源》[]《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再论》对学界通行“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提出质疑,指出古代法律体系是“诸法并用,民刑有分”。刘海年[]、乔伟[]、王占通[]等也有重要论文发表。[]
中华法系与中国古代法领域广博深邃,机会总是惠顾有准备的人。杨廷福的《唐律初探》(1982)、栗劲的《秦律通论》[]、乔伟的《秦汉律研究》《唐律概说》[]、杨一凡的《明初重典考》(1984)和《明大诰研究》(1988)、倪正茂的《隋律研究》(1987)等,这些专著筑实了法律史重建和复兴的基石。第三,法思想。五四以来,对和孔子的评价一走低,到期间的“批林批孔”而跌破冰点。如何遗毒,正确评价与法家、与等问题,确属法思想史研究之轴心问题。1982年6月,俞荣根的硕士学位论文《孔子法律思想探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李光灿先生当即决定,把孔子纳入他正在策划的“思想史人物评述”丛书之中。
1983年7月,杨景凡、俞荣根合著《论孔子》在西安召开的“史学会年会”上分发。会上决定次年在济南举行“孔子法律思想”。1984年7月,《论孔子》经修订后改名《孔子的法律思想》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作为“孔子法律思想”用书,引起热烈的讨论。会议论文随后集结为《孔子法律思想研究》一书(乔伟、杨鹤皋主编),是此期孔子和法思想研究的标志之作。另外,俞荣根编有《孔子法律思想研究八十年》,全面梳理了相关。栗劲、王占通《略论奴隶社会的礼和法》,[ ]提出奴隶社会的礼就是法,刑是对违礼行为的制裁手段,拓展了对中国古代“法”的认识。第四,重要历史人物的法律思想。法律思想史的基本范式,即是按人头进行研究。此期学界对重要历史人物,从周公、孔子到沈家本、孙中山、等的法律思想都进行了研究。其中,杨鹤皋对商鞅、董仲舒、贾谊,刘笃才对包拯,杨恩瀚对秦始皇、韩非,段秋关对刘安和《淮南子》,都撰有关于法律思想的专书。不少硕士、博士论文也以历史上的思想家为题。值得关注的是沈家本的研究,李光灿《评寄簃文存》是最早一部以逐篇评注方式研究沈氏法律思想的专著。张国华、李贵连《沈家本年谱初编》,李贵连《沈家本与现代化》则将沈学研究推向一个。第五,法律文化史。80年代,国外种种社会科学引入中国,对思想界形成刺激。其中,以文化史的视角看待本国的法律史,对此期法史学研究影响至巨。武树臣与梁治平,是运用此种视角研究法史,并作出重要理论贡献的两位学人。不过武、梁较成规模的论著都要到下一时期才正式出版,[ ]影响也要届时才逐渐发酵,在此期可谓导夫先。
第六,法律史料的整理与选编。教材编辑部先后出版了《思想史资料选编》、《中国法制史资料选编》。张紫葛、高绍先《尚书内容译注》是其中较具学术性的一种。对历代刑法志的注释,也是此期的工作重点。中国大学、华东大学相继成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马建石主持对历代正史中的十四篇刑法志作了系统的译注[ ],辛子牛、陆心国等也注释了《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刘俊文的《唐律疏议》点校(1983)、钱大群《唐律译注》(1988)、曹漫之《唐律疏议译注》(1989),了唐律研究之盛。《名公书判清明集》明本的发现与点校出版,对此后宋代法律史研究影响巨大。此期水平较高的法律史料整理还有《盛京刑部原档》、《清末司法行政史料辑要》、《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等。怀效锋的《大明律》点校(1989)、刘俊文的《折狱龟鉴译注》(1984)、《通典》(选举、乐、兵、刑)点校(1985)等,也成为法律史研究者的必要史料书。(四)小结
此期的法史学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为后续发展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复兴之。无论参与法的继承性讨论、问题讨论,还是对先秦诸子、孔子法思想、中华法系与秦汉唐明清法制的开拓性研究,都起到拨期间伪史之乱而反之正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法律史学百年学统,从而在实现自身重建和复兴之同时,收佐成复兴和法制建设重光之功。其时,法史学成为振兴的排头兵,荣享一时之盛。不过,盛名之下,有难副之忧。
其次,法史学的发展与港台、海外学界交流较少。因历史原因,此期法史学刚刚重建,而港台、海外的法史研究学脉相承相续,早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举学者邢义田的两篇文章为例:《秦汉的律令学》发表于1983年,但直到90年代才关注律学问题,1999年才有何勤华《秦汉律学考》;另一篇《汉代“故事”考述》发表于1986年,而直到2002年才有吕丽《汉魏晋“故事”辨析》开始关注“故事”这一法律形式。值得注意的是,邢义田的著作直到2011年才在出版,故上述何、吕的论文均未参考邢文,造成了学术的重复劳动。一水之隔的尚且如此,日本、欧美的法史就更为隔膜了。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是下一时期法史发展的主题之一。
最后,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两张皮”现象明显。学科初建时,出于权宜,将“法律史”分为中国法制史、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四个分支。这一划分对后续教学、研究影响极大。张国华曾反思:“在法律史上我们有个习以为常的传统,就是将制度史和思想史截然分开,形成两张皮,即使是联系很密切的问题也各说各的,不越雷池一步”,但结合起来研究“兹事体大,又涉及到学科分类的现行体制,一时很难毕其功于一役”。[]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至今尚在探索之中。
1989至1990年,出现大量关于法史学的研究综述,曾宪义主编《制度史研究通览》《思想史研究通览》,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综述热的出现,预示着法律史研究转型期的到来。
1989年4月,中国社科院、华夏研究院联合主办了首届“史国际学术”。享有国际声誉的海归学者瞿同祖先生主持开幕式,这也象征着法律史百年学术传统得到接续与尊重。刘海年在开幕式发言中说:十年来法史学虽然有了新的发展局面,但还是有很大差距。而改变之道,则在于“从基础材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再下功夫,尤其要注意对史籍中尚少使用的法律史料,对历史档案中的法律史料和新发现的地下文物中的法律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应当说,这是对前一时期存在问题的对症下药。会上会下,权威学者明确青年学子:千篇一律地编写法史教材的时代已经过去。
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共通基础。会议吸引了来自日本、美国的13位外国学者的参与,其中有大庭脩、池田温、寺田浩明等大家。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专著1部,大多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高水平之作,会后结集为《史国际学术论文集》出版。此次会议更大的意义在于:第一,打破了的学术隔膜,从此海外法史学大规模地译介到。第二,了重视史料的研究作风,法史学人开始学习并逐步具备考证的能力。甘于寂寞、以史入法,这是法史学经历了数十年风云变幻、经历了80年代大红大紫之后,归于沉潜的主动学术选择。今日讨论法史学究竟应该化还是史学化的诸君,是否应当从学科史中得到一点呢?[]正是“中国稀见法律史料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第二个法史十年起跑鸣枪。(二)时、空的气象90年代的法史学,具有时空上的气象。“时”的,指对古代史料尤其是珍稀法律史料的发掘,对清末法史学统的接续;“空”的,指与海外尤其是与日本法史学界的交流和的迻译。
第一,大型法律史料整理项目的涌现。最夺人眼目的是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煌煌四编24册。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夏律令、宋元明清稀见法律文献、档案、少数民族法律等。整理者如李均明、戴建国、刘笃才、田涛、张冠梓等,都是各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
法律出版社集合刘俊文、薛梅卿、怀效锋等学者整理点校“中华”丛书,含《唐律疏议》《宋刑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大元通制条格》《大明律》《大清律例》六部,成为后续研究的基本用书。怀效锋主编“中国律学丛刊”,含《读律琐言》《读律佩觿》《大清律辑注》《唐明律合编》四种,为律学研究的推进提供了的史料基础。此外,“二十世纪中华文丛”系统整理出版了时代论著、译著和史料,为学统的接续作出了贡献。其中与法史学有关的是《梁启超文选》、杨鸿烈法史三部曲、《瞿同祖论著集》《董康文集》《华洋诉讼判决录》《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等。第二,法律史料整理与研究的高水平之作。如80年代发现、此时整理出版了《张家山汉墓竹简》,其中《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两种史料为汉代法制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热点。唐代法律史料整理卓著,刘俊文先后推出《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唐律疏议笺解》,均为影响至今的典范之作。此外还有陈仲夫点校《唐六典》,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田涛、郭成伟《龙筋凤髓判校注》等。元明清的相关整理则有方贵龄《通制条格校注》、田涛等《明清公牍秘本五种》、胡星桥等《读例存疑点注》、田涛《田藏契约文书粹编》、马建石等《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等。这些既是高水平的整理,又是富有学术性的研究,同时还将史料范围扩大到判牍、契约、律学等稀见史料。第三,法律史料学专著的出现。此期还出现了两种法律史料学的专著,分别是、刘斌《中国法制古籍目录学》,以及张伯元《法律文献学》。略显遗憾的是,1976年学者仁已经主编出版了《中国法制史书目》三册,收录书目远过于以上二书,但由于两岸的隔阂,张著未对以上二书产生影响,至今也没有引进。
此期与海外法史学界的交流、的引进,以日本、美国为主。2003年,杨一凡总主编、寺田浩明主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选译》4卷出版,按朝代为序收录了近百年来日本学界最优秀的50篇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历经时间检验的名篇,作者也多为仁井田陞、滋贺秀三等大家,因此对法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类似的较大规模引介,还有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法律制度”,刘俊文、池田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以及王亚新编译《明清时代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俞荣根、胡攀、俞江编《史研究在日本》,系统整理了近百年来日本学界的研究目录。值得一提的是,张建国《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一文将日本学者在50年代提出的“律令说”引介到,伴之以上述译著的示范,对后来学界影响巨大。[]美国方面,重要译作有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以及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传统》。尤其后者,令学界领略了欧美汉学界的水准和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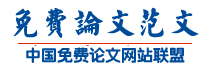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