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WCP,8月13-20日)已经在完美落幕,在此前、中、后,文汇报文汇讲堂工作室联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大哲学系共同向呈现丰富多彩的“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录”。同时欢迎参与同步推出的“我爱WCP”有活动。(见文末链接)
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的影响至深,哈贝马斯在场,霍耐特移居美国。昨天,在大本营的第三代重要代表卢茨-曼为我们梳理这个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的前世,三代传承故事和学术一手资料着实珍贵。今天,我们迎来了为期26天的系列录的压轴,也是终结篇,看看法国哲学大家德贡布。感谢所有读者的始终陪伴,今晚6:30-9:30,华东师大科学会堂,微型“世界哲学大会”移师124期文汇讲堂,优秀的意大利、美国、中国哲人同台共话东哲学与你我,机不可失。(详见文末报名链接)
“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录”(25)
被人: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教授,以下简称“德贡布”
在1980年英语版的《当代法国哲学》一书的序言中,贝利奥尔学院的阿兰·蒙特菲奥(Alan Montefiore)这样称贡布:一个本族的向导,既能对他自己的领域有专门知识,又能和他自己领进来的穿越这个地区的陌生人有真正的交流,德贡布就是这样的好向导。
75岁的凡桑·德贡布在40年前的这部著作之后,又以《所有类型之对象的语法》《心灵的食材》《意义的机制》《主体的补语》《熊的推理及其他实践哲学论文》《身份的困境》等十几部哲学著作,收获在法国乃至英美学界不俗的反响。他的“哲学交流”跨越语言哲学、行动哲学、社会哲学、哲学、主体哲学等多个领域,是法国当代哲学界毫无争议的领军人物。
长期执教于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EHESS)的德贡布不仅深悉古希腊哲学、观念论、分析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传统,并且在这些传统之上发展出了自己关于社会性、意义、主体、行动、身份等问题的独到观点。我曾有幸受其言传身教,屡屡惊叹于他精炼的论证风格、对思想史和文本的精深理解、思想建树上的率直,深为其跨越门派影响、兼具深刻人文关怀和全球视野的气度所感染。
德贡布为人质朴,不爱以第一人称论事,更不爱谈论自己的所作所为。借世界哲学大会之机,我们有幸访问到他。他对于战后至今的法国哲学直言不讳,对于自己的分析风格严格界定,尤其是对于自己的社会学关怀细数由来,为中国读者展现了法国当代哲人打破流派、扎根传统、立足现实,既严谨又的思想风尚,而“二阶的普世主义”是他近年来的主要观点之一,代表着欧洲思想家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对于不同社会文化间对话所负有的责任感。
德贡布近年来的主要观点代表着欧洲思想家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以及对于不同社会文化间对话所负有的责任感
文汇:您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哲学史上,人们通常把现象学、分析学、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在这一时代的汇聚称为所谓的“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在国外,您时常被视作是法国哲学黄金时代(法国理论)的继承人。
中国读者对您的了解大多是通过您的早期作品——阐释法国哲学的《当代法国哲学》一书,然而,在法国您以引进并运用分析哲学而著称;与此同时,您所关注的问题很多都属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莫斯(Marcel Mauss)、杜蒙(Louis Dumont)、奥尔蒂格(Edmond Ortigues)的范畴。这一切使您的思想具有很鲜明的独创性。是什么样的哲学训练郑伊健和梁咏琪促成了这一独创性?福柯(Michel Foucault)、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等这些思想家是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德贡布:我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索邦大学完成哲学学业的。我接受的是法国式的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主要所学就是法国哲学。今天仍然占主导的法国式哲学教育非常重视对哲学史及对作者的掌握。在我们那个时代,学生们被要求深入了解的那些大哲学家是战前观念论——一种法国式的新康德主义——所推崇的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我从来没有上过关于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的课,更别说关于中世纪的思想家了。就此而言,今天的情况大有改善了;另一个今昔重要区别在于,现在我们的课程中还有普通心理学和普通社会学。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福柯都是授心理学开始他们的大学职业生涯,两人对一种人文科学的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您提到了好几个思想家的名字。在索邦,我上过德里达的课,他当时是利科(PaulRic?ur)的助理。我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了解都归功于上利科的课程,他每年都详细地胡塞尔的一部大作。在这些名曰“实践工作”(意味着学生可以提问题)的课上,当时还没有发表任何作品的德里达教我们深入地阅读文本。他在评述经典文本的时候会非常耐心地考察一段文字可能有的所有含义,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刚才问我,当时我们对于将对下一代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思想家有多少了解?说实话,今天回想起来也会有些吃惊:当时我们进入思想世界是两种并行不悖的途径。一方面,学科学习存在着正统的教学:为了通过考试继而找到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即为了学术生涯,这些课程的学习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学生间存在着一种前卫的反正统文化,交汇着海德格尔、马克思的思想,结构主义一直具有吸引力,但我们只能靠自己去掌握它们。因此,一方面是了解经典的学说和理论,如斯多葛主义、康德主义等,另一方面是每个人为了发展自己的思想而展开个人阅读,因此这些阅读有点冒险和的意味。
我的第一本篇幅很小的书,是1971年依据第三阶段博士论文而改写出版的《柏拉图主义》。今天看来,它就是法国式哲学教育的纯粹产物。但我在1977年出版《当代法国哲学》时,已经开始怀疑这一法国传统了。
德贡布:我怀疑我们那一代人从后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或“法国理论”的流派中能获得什么。这个倾向贯穿于全书,并且在最初的几页就已经流露出来了。尽管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处在某种理论的同盟中,其实像当时所有法国人一样,我对于那些思想家之间展开的论争之绚丽和精致叹为观止。但我感到这些论争其实是在一条死,这些哲学家陷入某种竞争中,这种竞争恰恰与他们所受到的“法国式”教育有关。这种教育带来了这样一种观念: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哲学,我们能够通过观念史的进在其中调和所有的伟大思想家,并得出某种类似意识或思想之进步的东西。这种打了折扣的“黑格尔主义”自然而然地令人以为具有创造性的哲学已经走到了尽头,所有能被说出的重要的思想都已经被说过了,我们着“哲学的终结”,这一主题常常被当时的法国“海德格尔主义者”借用。这一终结是巅峰还是死亡?大家的意见不同,但重要的是不管情况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想要从事哲学的人都来晚了一步,剩下的唯有历史。
除非是大胆地相信自己有能力不受整个传统的——通过一种比所有距今为止所提的问题都更彻底的提问方式,而这恰恰是战后多位最优秀的年轻哲学家(您所提到的福柯、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利奥塔)想要探寻的道。他们的想法是,必须想办法摆脱整个哲学传统的所有预设(换句话说,所有)。由此产生了一种冒险,它是一种对于彻底性之竞争的结果:质疑这个或那个原则还是不够,还要质疑所有可能存在的原则的总原则,所有预设的总预设,以此在所有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占领制高点——以此来证明那些竞争对手仍然都持有这样或那样的,仍然被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方式所“”。一言以蔽之,他们仍然不够彻底,仍然能够被超越。这一竞争在我看来导致一种思想上的。我从中所看到的不是某种超常的生命力,而是一种特定传统的衰竭,我希望从中出来。
德贡布:1969年,借兵役之机(我们也可以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完成它,而不一定要去部队),我在大学教了两年书。也是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第三阶段论文,内容是关于柏拉图。我是在那里发现了关于古希腊的分析哲学。令我惊讶的是,较之我以“法国式”的知识背景所能做到的,我必须承认分析哲学家能更好地理解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问题。
面对一个古典文本,分析哲学学者直接进入文本所提出的问题。这恰恰是我的一些法国同仁所不满的——“你们能想象吗?他们想要把柏拉图变成一个同时代人!”就好像把一个柏拉图讨论过的问题(比如,“一”与“多”的问题和虚假命题的可能性)当作一个对于我们而言有意义的问题来讨论,当作一个我们自己提出而柏拉图能为我们解疑的问题来讨论,这其实是在降低柏拉图的能力。但如果我们要将柏拉图当作同时代人,那么我们得将他想要说的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不仅仅是引用他或将他从希腊语翻译成法语,而是将他翻译为一种我们能为之负责的哲学语言。
2017年10月,德贡布在法国希腊研究所的上,就欧洲认同问题,即欧洲是否承认他们拥有欧洲身份展开讨论
在1980年,我读了恩斯特·图根德哈特(Ernst Tugendhat)于1979年出版的大作《意识与》,我的一个朋友觉得我一定会对这本书感兴趣,从把书带给了我。这番阅读对于我具有决定性影响,因为它告诉我:我们能以创造性和多产的方式令观念论和语言分析哲学对峙。除了他就意识所得出的特殊结论之外,图根德哈特还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所倚赖的文本,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黑格尔或海德格尔,我们可以持有一种纯粹的哲学态度。我们可以在阅读他们的同时,要求他们回答我们的问题——只要问题确实涉及他们自己曾提出的疑问。图根德哈特是第一批做出这种尝试的人之一,但我们能展开一种“分析康德主义”(如斯特劳森Strawson)或“分析黑格尔主义”(如布兰顿Brandom、麦克道威尔McDowell)的想法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了。
文汇:这一转向的第一个是您的《所有类型之对象的语法》(1983年)。在那个分析哲学进对于法国哲学家还很陌生的年代,您通过此书想要告诉他们什么呢?
德贡布:我在书中尤其强调了两个观点,它们在当时对我很重要,使我彻底反思我们从事哲学的方式。第一个观点:语义的问题应该先于认识的问题。第二个观点:分析哲学的分析性在于它通过分析语言来分析概念,但它所分析的语言是话语,其单位是命题,而不是词汇,命题的单位是词语。
关于第一点,就像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继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之后所重申的,整个近代哲学都建立在认识论问题的优先性之上。首要问题在于——面对笛卡尔的怀疑,如何去证明我们的判断并加以确定。但这一点完全是可以去质疑的。因为达米特只是将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中所隐藏的一种观点明确地表述了出来,即,在能够提出“如何证明一个命题”这一问题之前,先要能够确定它说的是什么,以及它在现实面前对什么负责,亦即说明它的真值条件(它的逻辑真值条件,而不是它的认识论验证条件)。为了能够对一个命题提出怀疑,先要有能力理解它在说什么——这就是广义上的逻辑(不仅是关于推理的理论,而且是语义学,即对于表意模式的研究)相对于认识论的优先性。
德贡布:我觉得这一“语言学转向”较之那些想要成为最大胆者的法国哲学家的哲学竞争更彻底,同时又更谦逊。所谓更彻底,是因为它质疑的是他们自己不敢讨论的近代哲学核心(认识论的优先性);所谓更谦逊,是因为它将我们带入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情景,我们在其中必须先问我们的对话者——你要说的是什么?
关于第二点,在20世纪60年代,所有的人都已经承认思想和语言是不可分的(但梅洛-庞蒂会否认这一点,他在这个问题上忠于柏格森)。但我从图根德哈特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学到了,上述观点还不足以赋予哲学以分析进所需要的方法。图根德哈特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完全把握到了这一关键的问题:对分析进的哲学家,当我们与他们谈论语言,他们想到的是词语,而分析的对象当然是命题。在必须从词语着手这一观点的背后,我们实际上能发现的是维特根斯坦要质疑的那个,亦即这样一种天真的想法,它认为语言从根本上是一些词语的集合,这些词语命名我们周围的事物。分析一种语言肯定是考察词语并追问它们的意义,但这意味着考察它们在话语,亦即广义上的命题(不仅是陈述,而且也包括疑问、假设、命令)中的功能。
文汇:您后来所有的著作中都贯穿着上述两个观点,但我们在其中还能发现一种对于社会学问题的不懈关注,尤其是在《心灵的食材》(1995)、《意义的机制》(1996)和《身份的困境》(2013)中,它们已经成为了社会哲学的经典。您是如何想到对社会性的关注的?
德贡布:我从一开始就对社会哲学感兴趣。我在完成哲学学业的同时也修了社会学的学士学位。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哲学学业在当时包含一部分人文学科的基础课程。人文科学在当时还没有完全脱离它们的哲学源头。由此产生了福柯后来在《词与物》中所针对的想法——统一所有这些知识的想法(莫斯会说,一种关于“总体的人”的科学)。这个统一的科学需要哲学基础。梅洛-庞蒂在索邦大学的课程(这些课程现在已经以《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1949-1952年索邦大学课程》为题合并出版)上曾将经验现象学奉为对这一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只是接受了这一规划,但我将梅洛-庞蒂所定义的那种关于意识的描述性哲学换成了一种关于行动的分析哲学,它部分取材于维特根斯坦和亚里士多德(安斯康姆在《意向》中所诠释的那个亚里士多德)。
在当时,了解人文科学的基础是一个哲学学生白天的正常活动。但有些晚上,在“社会主义或”团体中,我们与卡斯托利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一起讨论他正在撰写的关于历史理论的文本(它们现在是他的《社会的想象机制》的第一部分)。卡斯托利亚蒂斯发展出的观点是,一种得到充分理解的文化人类学能够引导我们彻底地更正我们对于马克思和《资本论》,对于历史决这一想法本身的判断。而这会赋予这些人文学科以深刻的意义:历史哲学能从中获得什么?
因此,我对于社会哲学的兴趣源自所有这些契机。我当时提交了一个国家博士论文(所谓的“大论文”)的题目。那个题目是关于社会学的起源——不是指历史意义上的最初的开端,而是指社会学这一想法出现的那一刻,对于一种社会科学的需要被意识到的那一刻。
我的“大论文”的构思是,社会学的想法本到一种悖论的。这一悖论被写入了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名称中:“社会”一词来自法律,它指一个契约联合体,但社会学——真正的社会学——其生成是为了对于社会纽带的这种个体主义的构想,后者是近代契约论的构想。我想通过这篇论文证明,在社会学学科的内部存在着一种建构性的张力,它在那些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中既构成其意义所在,又时常成为其矛盾之处。
在1977年,我读到了杜蒙(Louis Dumont)关于现代经济观念之产生的著作《平等人》。杜蒙在当时因为他对于印度种姓制的研究而成为结构主义的权威。我读了刚出版的《平等人》后意识到他处理的就是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而且如果是我来处理的话做不到他那么好)!所以,我想要研究的问题是有价值的——既然它们被一个社会人类学大师处理了。我要做的是重拾杜蒙所留下的问题——但这一次是从哲学的角度(概念分析的角度),而不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因此我必须将我的“社会哲学”研究线索和我的“语言哲学”线索拧到同一种研究中,这要求我展开巨大的工作。一直到《意义的机制》(1996),我才觉得自己有能力令语言和心灵哲学服务于社会哲学。
文汇:所以您并没有放弃您的大论文题目。恰恰相反,它在《意义的机制》中,更普遍地说在您的社会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您能不能进一步展开这个问题?
德贡布:有一个概念能概括到社会学的那个悖论:关于社会的“集体个体(individu collectif,法语)”概念。从严格意义上理解其学科的那些社会学家想要研究真实的社会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单纯互动。他们因而想要谈论社会总体,将人类群体视作具体的总体(totalité)。然而,这些社会学家同样具有现代思想,因此他们与同时代人(与我们)一样认为一个人就是一个个体。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些观点都是成立的——确实存在着社会总体,现代人确实将自己视为个体(在这个词的规范性意义上)。怎样调和这两个观点呢?包含社会契约在内的哲学的做法是给自己造出一个公意的集体主体,这一主体是一个集体个体,因为它能够说“我们想要”。由此,社会成为一个集体个体,亦即一个由一群个体构成的个体。但这个概念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如果构成一个复杂体的组成部分保留它们的个体性,那么它们所构成的总体只可能是一个聚集物,是诸多可识别元素的组合,而不可能是一个能在时间中被个体化的存在。
通过集体个体的概念,我从纯粹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杜蒙所关切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哲学家对于总体概念所言甚微。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所针对的是观念论思想家。从根本上,他想说的是后者停留在康德在机械总体和有机总体之间所建立的对立上(在《判断力》中)。然而,社会总体既不是一个机械体,也不是一个有机体。因此我们需要设想另一种总体及另一种总体和组成成分间的关系,以便能够证明——与机械体不同,社会总体先于其组成成分。
总之,我试图回应的是杜蒙自己的要求——让哲学家帮助我们就总体的形式构成问题明晰我们的概念。这是我通过分析哲学的手段所试图从事的。
文汇:以同样的方式,您不仅为社会性问题、而且也为主体的问题(《主体的补语》)、行动的问题(《熊的推理及其他实践哲学论文》)以及身份的问题(《身份的困境》)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您是通过哪些语法(哲学意义上的语法)工具来为这些重大的哲学问题带来新的生机,将它们变成自己的问题的?
德贡布:哪些语法工具?您要问的是,我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汲取了哪些灵感?首先我要明确的是问题绝不在于将属于哲学家的问题转手给语言学家。我们应该使用的是同一部哲学语法。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课程中曾这样解释:以“好”一词为例,人们会以为,我们应该问的是“什么是好的?什么使得好的东西具有好的属性?”没错,但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总不至于去考察不同的例子,如一锅好汤、一番好的行动、一本好书、一个好的等,并在其中寻找同一个“好”的属性。维特根斯坦让我们将一部哲学论述想象为语述,亦即一部关于句子成分的作品。这个“句子成分”的概念(partes orationis)来自拉丁语法,指的是在我们的句子(它们构成我们的话语)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等。但维特根斯坦解释道,哲学语法的论述会包含一些对于哲学家有用,不为语言学家所知的章节,后者不需要它们来研究人类语言。例如,其中会有一章是关于人称代词(“我”、“你”、“他”、“她”、“我们”等),它尤其涉及令第一人称有别于第三人称的原因。其中还会涉及到两种形式的第三人称自反代词,直接引语自反形式(“约翰给自己刮胡子”)和间接引语自反形式,后者指向第一人称(“约翰说自己准备好出发了”就相当于他说“我准备好出发了”)。哲学家应该在这一关于人称代词的章节中分析我们关于人类主体的概念。
至于您提到的其他概念,应该将它们归入它们所属的“成分”。人类行动的概念应该被放入关于某些行动动词的章节中,这些动词具有如下的特征:如果我们想要用它们来描述一个行动者在做什么,我们必须要能够赋予这一行动者以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知识(我们不能说某人正在结婚,但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知识,但它是特殊的知识,它是第一人称的知识,而不是观众或观察者的知识:通过这一知识,行动者知道自己在做他有意向做的事情,通过这一知识,他恰恰因为在执行自己的意向而知道它。总之,它是安斯康姆在《意向》中所称的“实践知识”。
至于“身份”概念,它从属于关于疑问词的章节,尤其是关于“谁?”(哪个人)一词的那一章,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要么它是关于某人身份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问的是:他叫什么名字,涉及到的是谁?),要么它是关于某人对于自己的看法的问题,是关于他认为自己是谁及他想要是谁的问题(就像当人们问:他把自己当谁啊?)。在第一个含义中,“谁?”可以和“他们中的哪一个?”互换,但在第二个含义中,它不可以(如果有人说“我想做我自己”,我们不能问他:你想要群中的哪一个?)
文汇: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正在举行。其旨之一在于哲学入世(即我们共同生活的单数意义的世界)。您的思想涉及自律、行动、社会纽带、个人和集体身份等入世的问题。借此机会,我们想问您,您是如何看待哲学和当今世界的关系的?
什么是哲学,什么不是哲学?类似“什么是科学、教、”等问题,用两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能发现,“哲学”一词可以从两层意思来理解。我们能将它理解为对于世界的一种广泛的认识,它出自个人思想(想要探讨一个群体或一种文明的哲学是很难的,除非我们赋予它们一种个性,将它们描述为集体思想者)。亦或者,“哲学”一词能被用来指称一种反思活动,它所运用的是一些由古希腊思想家所发明的概念分析方法,今天,这些方法仍然具有希腊名称,如“(dialectique)”、“分析(analytique)”、“本质(eidétique)”等。
这一反思的活动并不任意或凭空展开,而是意在令我们摆脱在这样或那样的领域中的知性困惑,他们来们的科学进步中、对,法律、伦理等问题的理解中等,从普遍意义上而言——在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中。希腊哲学家将他们用上述技术所处理的问题分为三类:逻辑的问题、物理的问题、伦理(包括的广义上的伦理)的问题。这一分类始终是我们能赋予作为学科的哲学的最好内容。
8月18日世界哲学大会上,法国汉学家Anne Cheng指出我们仍需反思“如何学以”这一传统核心问题,印证了德贡布的“哲学是对世界的广泛认识”之说,也反映了法国哲学者对多元文化的浓厚兴趣
上述对于概念的分析,或更确切地说对于概念体系的分析(因为一个概念不可能被孤立起来理解或研究),首先(不可避免地)是在一门语言或一个文化的范围中展开的。在我看来,当今这个时代下哲学家的主要问题。如何扩展我们的分析,以便在令我们获得思考能力的那个知性体系中将必要的元素和附加的元素区分开来?必要的元素是定义概念的那些元素,比如“因”、“行动”、“数”(这些是许多哲学讨论的核心概念)等。如果我们修改其中的一个元素,那么我们即使是保留了词语,也还是更换了讨论的内容。以哲学史上的一个人尽皆知的概念为例,我们可以就关系的概念发问:是否能简单地用一系列事件的规律性来定义它?如果我们满足于这样的定义,我们所运用的是否还是关系的观念,还是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意义上的“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内涵?有人会说,如果哲学活动这样进行,那么它将自己简化为对于常识的,甚至是对于某个时期某个背景中的常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从事被人们称为“日常语言哲学”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我们应该同样在自然科学、历史学、法律实践甚至任何我们需要使用“因为”的地方,考察我们的概念要求。而恰恰是在我们自己知性世部的语用多样性中,我们产生了绝大部分困惑,以及哲学家之间的广泛的论争。
然而,这一哲学分析是针对我们的概念作出的,它们是由我们的文化特有的知性体系所提供的,而这一文化是特殊的。当代哲学应该面对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开拓我们的概念研究。我们应该继续追问:在某个概念的运用标准中,有哪些是不能被改变的,否则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谈论主题。但对于在我们的文化中所找到的属于我们的概念进行追问已经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学会去追问,我们的概念是否也是不同于我们的其它文化中所使用的概念?我们的定义是否对于所有的文化都成立?换句话说,我们的哲学工作应该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汇合,后者将一个传统中的思想形式翻译为另一种传统中的思想形式。
以马塞尔·莫斯为创始人的那个比较人类学传统我们区分两种普世主义。一阶的普世主义是这样一些思想家的态度:他们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对于自身的单纯反思来得出所有知性体系都必须的概念要素。这种态度是很容易理解的,它对于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确实,如果我正确地思想,那么我所思想的似乎应该也是任何人对于同样的问题所抱有的想法。特殊的思想者因此相信自己能够直接上升到一种属于所有人的对世界的理解。为此,他只需要在先入为主的面前保持。
这种一阶的普世主义,启蒙的普世主义(在十八世纪的意义上)在今天看来是不够的。今天占主导的是相反的态度。后者是一种普遍的相对主义,其结果是,大家相信应该满足于生活在文化唯我论中——既然人类的文化(尽管都是人类的)不可能互通。
二阶的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立。它旨在将关于概念要素的哲学研究建立在翻译之上。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存在着翻译,这是事实。我们可以评估它们,这又是一个事实:没有任何翻译是完美的,但有一些比其它的好。翻译总是可能的(所以唯我论是一种),但如果不付出努力,我们无法实现或改善它。它是一种解释和诠释的工作,但也是一种发明的工作,它发明出更普遍的思想形式,后者令我们得以描述那些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所必须作出的改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达到所有知性体系(而不仅仅是某个特殊的知识体系)所必须的元素。
文汇: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它是的准则,但也在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它也透露着人文主义传统的气息。您刚才所说的恰恰在强调不仅仅存在一种的方式,还需要理解其他的方式。换句话说,比较人类学不仅仅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而首先是一种的学习过程,如果我们借用您的著作《人性——与飞利浦·德·拉哈的对话》的书名,这就是一种“人性”。
德贡布:关于中国思想和文明,想要直接参与到应该伴随着从汉语到法语和从法语到汉语的翻译的那种哲学工作中,必须读和说中国语言并同时研究你们的古典文本(原版)和你们的实践。我只能满足于我能够读的语言中可以找到的材料。我期待中国的知识(包括哲学家、作家、史学家等)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理解自身,并用一种我们能与他们分享的术语告诉我们。而这种术语需要我们共同塑造。
24位哲学家·预热你想和世界哲学大牛对话吗?请参加“我爱WCP(世界哲学大会)有”
24位世界哲学家(21)阿瓦尼:伊斯兰哲学,可以富有成效地对线)安乐哲:哲学的最后一站不是真理,而是智性对线)辛格:印度哲学并不神秘,在诠释现代中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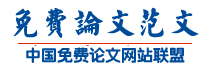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