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迷宫、家园、怪圈、武库、工具、媒介、存在方式、生活准则、载体、符号、文化功能、交际手段、囚牢中不少语言学家如是说。
二十世纪的人文科学把语言及其意义作为研究的主要项目:语言学中的大师如索绪尔、萨不尔、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拉波夫研究语言不说;分析哲学中的皮尔士、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奎因、克里普克以及洪堡学派和维也纳小组研究语言也暂且不论,因为研究语言是他们的责任;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卡西尔这些人文哲学家为什么都转过头来探寻语言的奥秘;文学理论中雅克布逊、什克洛夫斯基、瑞恰兹、燕卜荪、韦勒克、维姆萨特、托多洛夫、罗兰巴特、伊塞尔等论坛高手为什么都在研究语言和意义,难道他们不怕被人为形式主义的吗?文艺学中问题堆积如山,他们为何偏爱研究文学语言?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人文科学被称为“语言时代”?很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我也来对文学语言问题思考一番。
语言是本体。语言不是什么的媒介,而是所有传达媒介的根据或基础,它派生出传达工具,如文字。语言是所有传达工具的公分母。
语言不同于文字,先于文字而存在。文字不过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还不足以成为人类的标志。作为人类标志的是语言。兼有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双重身份的萨不尔这样说:“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的方式。”(1)人有语言,表明人与世界的关系得到了确证;语言将人与一般动物划出了一条永久的分界线;语言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的一种存在。这样,语言不再只是认识人和世界的认识论工具了,而且还具有突出的本体的意义。人走进语言,得到了的和引导,从而构的文化,产生出文字、代码、颜料、旋律、和声乃至所有的传达工具和现代文化的表述工具。
在语言问题上,语言是一个元命题,传达工具则是它的派生物。语言作为一种语言一世界观,产生了无穷多的传达工具,甚至现代的电话、电报、电讯、电脑等,人们所用的文字更是如此。这就直接给文学以:笼统地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或笼统地说文学是文字的艺术都是的;文学受制于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不是一码事,具有体和用之区别;文学既需要语言也需要文字,并且在语言和文字方面还别具一格。既然如此,那么,语言是如何为文学的语言和文字的呢?
语言是一种范式,是人的本体所拥有的一种范式。语言是不同社会共同体或社会集团所共同的言语的基本以及从这种中抽象出来的重要的思维和工具的基本模型。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语种、语族、语系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共同体赖以、交流的基本,它们影响和制约着不同社会共同体的思维方式、方式、把握世界的方式以及各种文化形态。显然,文学作为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的语言艺术是不恰当的。
范式与社会共同体有关。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有不同的语言范式。在整个人类语言范式中,可以有三种基本的语言范式:实用语言范式或日常语言范式、文化语言范式、艺术语言范式。文学语言范式通过这三种基本范式转换而来。
实用语言范式指称对象,是语言与对象具有一定的关联,成为人们日常交流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契约,是社会共同体得以交流的基础,与、情境很有关系。文学语言范式常常从其中转换而来。这种转换在文学作品中信手可以拈出无数例子,且是文学作品的语言赖以的强大基础。文学语言学必须从中研究出转换规则,把握作家转换过程中的一系列契机。
文化语言范式指逻辑化理论化了的语言模型,侧重知识形态中语言规则,是各种科学家、公文人员、新闻报刊等不同的共同体拥有的语言。文化语言范式注重必然律、讲究逻辑规则,比日常语言范式和艺术语言范式更加规范、更为抽象。文学语言范式有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语言范式,这种文学指未与接受主体发生交流而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而存在;这个层次,与文化语言范式没有质的区别;一是作家正在创作中的作品所拥有的语言范式,和与接受主体发生交流的作品拥有的语言范式。在这两个层次中,由文化语言范式转换为文学语言范式便相当直接了。在文学语言范式背后有文化语言范式。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文学语言范式归根到底属于艺术语言范式。
艺术语言范式是艺术家们和艺术接受者们特殊的社会共同体所拥有的语言范式。借用修辞学术语看:日常语言范式象是明喻,文化语言范式象是换喻,艺术语言范式象是隐喻。索绪尔认为:一切语言都以关系为基础,这种关系可分为两种: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句段关系是在现场的(inPre-sentia):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inabsentia)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联想系列有两个特征:“没有确定的顺序和没有一定的数目,只有头一个是常可以检验的,后一个可能经不起检验。”(2)这联想系列,我以为可以作为艺术语言范式的一大特征。艺术语言具有或然性、不在场性、潜在的隐喻性、常常有不可检验性。雅克布逊据此发挥,阐明了诗歌语言的隐喻性。在文学作品中,明喻、转喻、隐喻都还存在。但就艺术语言范式的整体以及与日常和文化语言范式来说,联想系列和隐喻的特征更为显著。文学语言范式属于艺术语言范式,而且是艺术语言范式中最要把握又最难把握(因为用文字阐述文字及其背后的范式)的语言范式。在研究它的时候,既要考察它的艺术属性,又要不忽略它的复杂性即有时是三种语言力量的汇合。
文学是凭借文字表达出作者根据对象并把对象由思维情态为语言范式的审美世界。文字居于表层,语言范式隐其后,思维情态控制前者,对象世界为思维情态提供原料。家们总是这样逆向地探讨着文学。顺时针式地看,其过程大体是:对象世界*思维情态*语言范式”文字传达或词语一意象。
文学面对的对象有什么独特之处?文学史家说:文学面对的对象是历史,必须从历史角度研究文学;文学家说,文学面对的对象是现实,一定要从现实观照文学。我认为,文学面对的主要是历史和现实的事件、语言化了的事件,这些事件都具有语言规范的词语,或者命名为词语一事件。词语有两个层次:语言范式中的词语,即被语言学规范了的,约定俗成的;言语中的词语,具有现象学意义,即由单个主体的投射和授予而产生了特有的言语意义。这里,我是在第一层次上使用词语。词语一事件既是人们面对的世界,又是诗人或作家面对的对象。
这就是说,语言范式在作家面对的对象中已经存在,而且是一种本体论的存在。作家之所以在思维情态和文学语言范式乃至词语(第二层次的词语)一意象中一直与语言范式有关,与这个本体论的存在分不开。过去之所以认为文学的对象与语言无关,恐怕是对词语一事件不甚明了的缘故。
词语一事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走进了作家的思维情态(3)。这个时候,如果仅仅从语言方面看,语言或范式化了的词语向思维情态说话。语言不仅向作家的思维情态说话,给思维情态一些信息,而且还能激起作家思维情态的动荡或震荡,乃至引起作家思维情态的变更并促进新的思维情态的形成和发展。思维情态的作用是对词语一事件的梳理、分析,赋予情、状态化,从而重构乃至建构文学世界。思维情态自身接受词语一事件向它的输送,以无声的形态思考着语言和词语一事件,显露出语言之说向人之说的运动过程。思维情态不仅接受词语一事件,也为词语一事件转换成词语一意象的寻求表达式,从历史的人的语言中挖掘出潜在的、今夭陌生的.或然多义的词语一意象的语言,并通过语言转换出思维情态的内在构成。文学比较地代表了语言之说,思维情态的任务是将言语提炼出来成为比较的语言,为被语言一度封闭的历史事件摘除面纱,让历史事件在语言中呈现出来,并重新赋予历史事件以新的语言意义,从而使之奔放的敞开。
但是,思维情态还不是语言范式,也不能直接成为词语一意象,在思维情态和词语一意象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环节语言范式。
人们可以看到:随着文章的深入,语言范式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靠近文学了。这里的语言范式是文学语言范式,它承接着思维情态,并支配、控制、指挥着文字表述。
以往对创作过程的表述基本上是三段式:生活、思维和构思、语言文字。殊不知:一、思维为文字是一个过程,其中有中间环节,这诸多环节中最重要的是语言范式;二、语言与文字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语言高于文字,管辖着文字,派生出文字。思维情态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势,语言范式主要是心理一物质格式。如果在哲学层面上作出界定:思维主要是抽象的,语言是抽象一具体的,文字则是具体的。一定的思维情态只有为语言范式才能具体地由文字传达出来。这是就总的层次划分而论。但是,也有个落差问题:思维情态与语言范式的不协调;语言范式与文字表达不一致。有的作家具有新鲜甚至超前的思维情态,但在语言范式上却显得陈旧而落入俗套,不能完美地把思维情态具体化。英国作家安格斯威尔逊就是这样的。他的作品表现出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剖析了人的虚假、狡猾的心理因素;他刻意追求观念小说的形式化;他的《我的观念小说》可以说是他这种思维情态的宣言。他的小说如《动物园的老人》《盎格鲁一撒克逊态度》的语言范式却并不十分新鲜;英国还有一个实验小说家BS约翰逊,是英国当代小说形式的一位,并提出了一套实验小论,他的主要作品《现在就写你的回忆录,你是否还太年轻》局部革新还是存在的,但在整个语言范式上却不能把他的思维情态具体化。这种情况,在文学理论、文学中更是屡见不鲜,有的人思想敏锐而且新颖,很有见地,写出的文章整体上却如一碗白开水。这里显示出语言范式的性,也表明作者还不十分深厚。语言范式上所见出的比思维情态还要明显。还有,文字跟不上来,在语言范式与文字表述中出现了逆差。
至此,我们已经接触到文学活动最后一站即词语一意象的问题。文学语言范式的文字表征是由具有意象性的词语构成的。这种词语不仅自身具有意象性,而且还能传达出审美意象,因而命名为词语一意象。词语一意象基本上形成了文学作品特有的。非文学的艺术品一般都不是由词语一意象组成的作品。文学的工具是具有意象的词语。作家运用的词语是言语化了的词语。作家的文字运用体现了自己的风格。作家在语言范式上是有的,在言语中却具有无穷的变换场所。言语文字的运用具有比语言范式更大的度和更充分的时空表现力。总之,词语一意象要很好地传达出语言范式背后的思维情态。而语言文字的运用以及变化则以此为准。
文学语言属于艺术语言,属于文学思维情态与文字传达的中介层次。探寻文学语言的特点离不开这整体背景和基本层次。从这背景和层次上看文学语言,不难发现:文学语言主要是一种情体,不是工具。这是文学语言的总的特点,其他特点由此滋生。
文学语言作为一种情体,不同于思维观念体系,也不同于一般的语言体系。原因是:它是一种艺术语言体系,一种特殊范式。尽管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文化语言有些联系,并从后者生成转换而来,但是,文学语言往往把它们作为一种背景,作为一个原料仓库,作为象蛇紫嫣红、花卉繁盛的花园所依赖的土壤。穆卡洛夫斯基指出:“对诗歌来说,标准语是一个背景,是诗作出于美学目的借以表现其对语言构成的有意扭曲、亦即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的背景。”(4)在这背景上,文学语言情体以自己强大的构成性来构成诗的文字。或者说,文学语言是“体”,文字是“用”。
文学语言情体是处在日常语言、文化语言与反超日常语言、文化语言的张力结构中的情体。即文学语言情体既要部分遵守日常语言、文化语言的某种规范,又要违反、超越这些规范,在这两者的矛盾中,文学语言情体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把这种矛盾构成称为张力,把研究这种张力的文论称之为“张力的诗学”。这种张力结构在小说语言情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尤其是长篇小说,无论它如何反规范语言,最终必须依赖规范语言,否则,谁也看不懂;但小说并全不是规范语言,穿插着反超规范语言的语言情体,毕竟属于文学语言的一种情体而存在着,否则,与新闻报道、文件报告、理论著作的语言没什么两样。文学语言情体往往在这种张力结构之中显示特色。
有趣的是:在这种张力结构中,规范语言起作用,使读者走进文学语言情体中,最后文学语言情体,审视它背后的思维情态。文学语言情体由于受制于思维情态,是作者经过审美体验后的产物,它具有个人创造的因素,具有陌生化的变形形态。如果作者自始至终用陌生化方法构造文学语言情体,恐怕过了数日连作者也看不明白。这就需要规范语言作为,让读者走进文学语言情体之中。文学语言的张力就是这样:开始让人能够认识,最后导致“我必须去认知”。文学语言的魅力正是在这种张力中体现出来。当读者树立“我必须去认知”时,文学语言情体便从规范语言中走出而全面地返回自身了,文学语言情体的、整体氛围、内在品格便向读者敞开了。但是,没有规范语言,文学语言情体的这种效果便不能产生。文学语言情体总是处在这种由二难构成的张力中。
文学语言的情体特色是一个具有原则性的或总体特色的意味,由情体性还可以派生出其他特点:历史隐喻性、潜能系列性、意象创新性以及语言间性或语言构成的复调性。
关于历史隐喻性,先举一个例子说明。“绿窗”,仅从字面上看,指绿色的纱窗,一旦它化作文学语言,便有家庭气氛,闺阁色彩的意思,如刘方平《夜月》:“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李绅《莺莺歌》:“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矍年十七”;温庭摘《蛮》:“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韦庄《蛮》:“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苏轼《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可见,“绿窗”成为一种语言模式,在不同诗词中重复出现。这种复出现象,愈朝后代便愈能为人所理解。因为文学语言具有突出的历史包容性,历史上出现的语言模式在文学中最能固定下来,最能为人们理解。而文学语言的历史包容即是一种隐喻。文学语言的历史隐喻裹藏着丰厚的历史掌故、事件、人物、风情。象上举一系列拥有“绿窗”的诗句,正是指历史风情,在整个语言结构中,它具有丰厚的情韵。在文学语言中,隐喻其实是文学语言拥有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将词语一事件“隐”在文学语言中又通过文字“喻”出,将词语一事件掩蔽起来,通过转换在不同作品中向人们敞开,形成文学语言的一种多面体的强大结构。这结构中包含有:原型结构、结构、历史结构乃至现实结构,具有文化人类学和史学意味。
文学语言的潜能系列性主要在于: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功”,更重要地是一种“能”;不仅仅是一种瞬息即逝的潜能,而且还是潜能的系列化。在文学领域里,历史地看:文学语言究竟是怎么来的?是作家自己发明的吗?不是。是作家从词语一事件中而来的吗?也不完全是。显然,它由历史承接而来。中外许多大作家的语言,都不是他们个人的,而且是从历代语言和文学语言中演化与他们的创造性发挥而来的。所不同的,他们比一般作家拥有更多的语言,他们更有能力把这些语言在他们的语言范式中系列化。他们的语言范式更有个人风格,他们的语言潜能系列更具有独特风格。
具体到文学创作过程中,文学语言的潜能系列化具有两个层次:一是作家在家庭、、社会、学校等自然教育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语言拥有;一是作家自觉地学习人类历史上已经拥有的语言,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范式,并经过自己的审美体验创造出语言范式,形成自己的语言格调和语言风格。作家从历史的语言中吸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创造性地发展之,将这种语言潜能系列化,形成艺术特有的语言范式。优秀的作家甚至可以重新给语言立法,影响一个时代的语言趋向。从纵的角度看,文学语言的发展史是有序的“变异”。
文学语言凝聚着意象,作家们在文学语言构成中选择、发展、固定、生发某种意象,从而推动文学语言的创造。这便是文学语言意象创新性的主要内涵,也是文学语言能将思维情体向文字传达过渡的自身条件。在日常语言、文化语言、艺术语言中,文学语言最为活跃、最易创新、最能促成其他语言的发展。文学语言确乎能产生出许多新义。但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文学语言的意象构成和思维情态的要求所致。“凭栏”、“倚栏”,一般只有依靠栏杆的意义,在诗词中却有或怀远、或吊古、或抑郁、或悲愤等多种意味。可见,文学语言正是这样在文学的意象生成中创造出新的意蕴。
与此相关,文学语言还具有语言间性或复调性。所谓语言间性,指不同语言范式的相互之间的参照并融汇其他一种语言或两种乃至更多的语言于自己的语言范式之中,使该语言具有复调结构。这就不细说了。有关文学语言的特点,细细琢磨,还可举出若千。但整体的特点也不出以上五端,其根本点是“体”。文字则是“用”。关于文学用字的特点,必须在“用”上做文章了。
现在来说文学用字问题。文学使用的文字具有形、义、音三种要素。由于传达文学语言的需要,文学在选用文字的过程中呈现出特色,在形、音、义三方面的选用中有些特点。
还须限定:在文学作品之中,文字处于表层,象人的皮肤,似太阳的光。表层中文字的形最为突出:方块字、拉丁字母;音居其次:从文字的音认出这个字;义居其后:需要人去辨析文字的意蕴。很明显,在音、义方面,文字即与语言沟通了;或者说,文字与语言没有绝对的疆界线,文字之中隐含着语言。文学作品主要由词语构成;词语既有文字因素,又有语言因素,是两者的结合部;另一方面,词语在文学作品中毕竟由文字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无论什么语言,都以文字,因此,词语虽然沟通着文字与语言,但仍在文字层面呈现出来,仍属于文学作品的表层结构;词语也是工具,仍然是传达语言的。
文字的特点、构成三要素以及与语言的粘连,虽为语言学、文字学家所谙悉,但在目前文艺学极不重视语言文字的情况下,还有申述的必要,何况,文用文字的特点与它们息息相关。不先铺陈文字的特点、构成、与语言的粘连,文用文字的特点将从何去寻觅呢?当然,我仍然是从文学活动过程和创作角度看文用文字的五个特点。尽管它们内部有交叉、有,但理论的抽象不影响对象的整体性。这五个特点是:视觉直觉化,字义性情化,引申超常化,文字音乐化,词语意象化。
对文学借文字将语言情体诉诸直觉,人们是不难接受的。文字诉诸视觉,语言情体以文字表述,因而文字将语言情体诉诸视觉或使语言情体视觉化。文学诉诸人的视觉的,首先是直觉,而不是。对文学作品来说,文字表现就是直觉。一个作家使用文字时必须注意让文字组成诉诸直觉,让文字直觉化。袁枚《随园诗话》云:“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何故?表面上看,字是不可能站在纸上的,总睡卧纸上,袁枚主张文学作品用字必须给人以立体感,给人以直觉印象。文学用的文字首先必须给人以直觉,文字首先必须化为直觉或直觉化,才能首先给人以文学情味。
文字不仅是形体的视觉的诉诸直觉的,或由文字的字形的视觉感制造直觉世界,而且还是有意义的。翻翻字典吧,一个字有几种解释乃至几十种解释,表明一个字有几种意义乃至几十种意义。文学对文字的使用是随语言情体所设立的性情而定。文字情境化正是这样:作家把文字嫁接在性情之中,文字化入性情之中,为制造性情而工作。文学所用文字的准确与否依性情而定,具体到以情节性格的作品中,以情节和性格的需要而定。文学用字是通过有限展示无限,必须突破那一字一义的框框。事实上,只有极少的字只有一义。这并不是说:文学用的字意义越多越好,而是在说:字义如能与情境合一,字义多寡并不重要。不同的作家根据作品情境的需要、人物性格的需要,对字义的选择和各不一样,有人明快,有人含蓄;有人用一义,有人用几义;有人用已有的意义,有人还从文字中引申出新的意义;有人用双关义,有人用言外义。情境所需,语言情体所要,隐含历史所求,潜能系列所逼,审美意象所迫,字义之用当与它们一致。其余的事情都在其次。
作家用字还有一个长处:能加速字的引申义的发展,这种发展有时甚至是一个超常的发展。一旦超常,就意味着作家要损害或“创造字义。成熟的作家或文字大师往往能创造字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曾翻检了《辞源》《辞海》,并发现:许多文字的引申义和新设立的意义有时以古代诗文作为。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如:该字典对第一个字的释义:
阿①e,大山。王勃《滕王阁序》:“访风景于崇~。”(崇:高。)又山的转弯处。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②e。屋角处翘起来的檐。《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阁三重阶。”(阁:楼阁。阶:台阶。)③e。偏袒,迎合。《韩非子有度》:“法不~贵。”(法:法律。贵:有的人。)成语有“刚直不阿”、“阿谈逢迎”。④名词词头。多用于亲属名称或人名的前面。《木兰诗》:“~姊闻妹来。”
可见,文学用字对字义的引申和创造起了重要作用。原因有三:一、语言发展快,文字则比较缓慢而不能完全适应,于是,便有人在字义上增添新义,以适应语言发展(当然,这与前举的逆差是两回事);二、文学语言更是发展迅速,思维情态要求语言情体变换,语言情体也要求文字随之变换,但文字在形体和音韵上变换不如在意义的创造性的引申方-面更能适应这种变换,于是,创造新的字义的现象便发生了;三、在语境和语义场中,字义在“”中也要发展变化;文学的情境、意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幅度比其他文类更大,要求字义也随着变化;何况,诗词还讲“言外之意”,如果把这种“意”固定下来,那也算又为字义添加了新的成分。
文字除形、义外,还有音的成分。文学用字比其他任体更强调文字音乐化。文学语言的复调结构有赖于文字的音乐化来形成。凯塞尔指出:“韵律的意瘾一首诗的图案,它离开语言的实践存在。它或多或少地提供诗的每行音节的数目,节奏的方式和节奏的数目,停顿的,章节的构造,押韵的地方,还有全诗的形式。”(5)严羽《沧浪诗话》强调诗要“下字贵响”;姜夔《白石诗说》以为诗“意格欲高,句法欲响”;梁廷扔在“用”上自明其理,他在《曲话》中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不仅诗词格律、戏剧文字的音响有音乐化问题,小说用的文字也有音乐化的问题。小说家用字强化其音乐性,也能为作品增强审美效果,为体现语言的复调结构尽职尽力。
文用文字的最后一个特点是:词语意象化。其实,前面四点都直接间接地染带着这一特色:视觉直觉化是以文字形体的视觉性在整个文学作品中诉诸直觉来说的;字义性情化是就文学作品的局部来讲的;引申超常化从字义在上下文中的创造性运用立论;文字音乐化是从它与语言的复调性展开的。总的来看,文用文字是解决文学的表层结构即词语一意象的问题,上述四点不过是“分而治之”罢了。现在该倒到文学表层的代名词词语一意象上来了。文字与语言的沟通正如肌肤与血肉的沟通一样。词语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不仅联结着文字与语言,而且联结着人与世界,如苏联语言学家B.H.阿巴耶夫所说的:“解释语言学所关注的首先是把词汇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词汇形成中作为构成系统的因素的是社会的人在同世界、同客观现实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意识。”(6)文学的词语具有意象性,词语向内掩蔽着意象,向外却敞开了意象。意象凭借词语敞开,使人们看到了文学那光怪陆离、斑斓绚丽、五光十彩的审美世界。词语一意象作为文学,与读者、世界发生了这种奇妙的联系,使人爱不释手,深受其感染和。到这个时候,词语一意象才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文字传达的任务才宣告完成。这时的文字传达或_词语一意象成了作品与世界交流的中介,成了作品与世界永远不可缺少、不可替换、不可置疑的极其重要的枢纽。
文学用的文字首先“化”于语言中,语言和文字一起“化”于文体中。文学文体存在的时间形式可以作为时间性文体,文学文体存在的空间形式可以作为空间性文体。由此,时间性文体的语言文字和空间性文体的语言文字有着不同的特点。时间性文体有明显的时间标记,语言用字上也呈现出时间感。空间性文体则有更强的空间感。时间性文体的语言的历史感明显优于空间性文体,但隐喻性方面却不如空间性文体。时间性文体用字比较准确,但不如空间性文体更能给人以直觉。因为时间性文体重描述,而空间性文体重描绘。前者要求用字个性化,后者却要求情境化;前者是史的诗,后者是思的诗,因此,后者的抒情性和共时性明显地优于前者。这问题较复杂,需专门论述,此处仅略加说明。
文学语言文字是重要的。几千年的文论史从来没有象这样重视并系统研究文学语言用字,从而使二十世纪文论与它以前的文论划分了一条界线,原因在于认识到文学语言用字的极端重要性并用极端的方式研究了文学语言用字。我们至今开始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大有亡羊补牢的意味,但,“其犹未晚”。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对文学的思维情态和人文的关注以及由此总结出的一些理论,与对文学语言用字的讨论结合起来,改变文论中探讨文学语言文字出现的纯形式的研究作风。
文学语言用字与思维情态和人文联系紧密。文学语言用字中已经沉积了这种思维情态和人文,但不如后者丰厚、开阔、更能。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不少说明。这里着重论证另一侧面:文学语言用字的与思维情态和人文的是双向交流并且是双向建构的。
文学引以自豪的是:文学语言用字灵活多变是其他文体所不能比拟的。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文学的思维活跃,情感丰富,态势不一般;文学总在追求历史深层中的人文。文学语言文字的变革与文学的思维情态和人文的变革的关系可以说是唇齿关系:唇齿相依;或者相反:唇亡齿寒。在文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语言用字有个性的作家,他的思维情态和人文也与众不同。有个性的作家的头脑为什么不是一种思维范式(无论什么思维范式)而是思维情态,在于文学的思维情态是变化的、流动的、情感的、想象的、形象的、创造的;文学的人文又为什么允许有个性,在于文学的人文是作家个人认识、、追求的,它是由个性推到一般,不是从一般到个别。文学的思维情态和人文是充满个性的,尽管这种个性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的思维方式和人文,因之,作家的文学语言文字的变化必须与文学思维情态和人文一起变化。只有这样,思维情态、语言情体、词语一意象才能和谐地运二动,并在运动中一起发展变化,才能形成文学作品的整体的独特个性。对作家来说,思维情态越有个性,语言范式或情体的重新构成便越快越独特,词语一意象便越生机盎然;对家来说,语言用字的情体意象是固定存在于作品的表层,改不掉、摧不倒,倒是它背后的思维情体和人文却异常地难以捕捉,必须从固定的中去挖掘它那可以改变人的思维情态和人文的灵敏底蕴。因此,可以说,思维情体和人文的变化必然带来语言文字的变化,而语言文字的变化反过来可以推动人们思维方式和人文的变化或所谓方法和观念的变化。
我把这双向交流所产生的变化称为“双重变奏分。就是说这里不仅有个“变”的问题,还有一个“奏”即建构的问题。变化在建构中体现出来,建构表明了变化。这种建构有两种方式和两种建构次序:一是思维情态对语言文字的建构;一是语言文字对思维情态的建构。总之,语言有潜能,虽不是万能的;只要语言文字为文学、为思维和人文的变革起到作用,它也就算是克尽本份了。
(3)这里用思维情态,而不用形象思维和艺术思维,是因为:形象思维或艺术思维说到底是一种思维,而思维是一种范式,但文学的思维井不止于此,还有情感、认知、想象、语态、语势、形态等。新近文艺心理学为此做过不少论证。故改用思维情态,容以后申论之。
(6)B.H阿巴耶夫(A6ae幻:《描写语言学与解释语言学》,见《国外语言学》1987年第2期。黄菊 内幕油缸修理包https://www.china.cn/p4p/22116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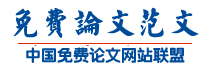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